快递员胡安焉:工作中的处境一点点地改变了我
齐鲁壹点2023-04-17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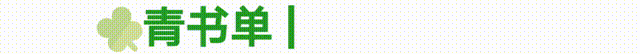
2020年初,刚失业的快递员胡安焉写了一些随笔发表在网络上。其中一篇记录他在广东某物流园干夜班拣货工人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豆瓣上反响热烈,获得数十万点击量,并被媒体广泛转载。后来,胡安焉将自己另一份工作经历——在北京送快递,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读库2103》上,收获了读者热烈的反馈,有读者称“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看完北京快递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内心像核爆一样”“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近日,胡安焉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除收录上述两篇长文外,还新增八万字篇幅,回顾他近10年间做过的其他17份工作——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加油站加油工、保安……他将日常的点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记录了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的辛劳、温情和正气。

《我在北京送快递》
胡安焉 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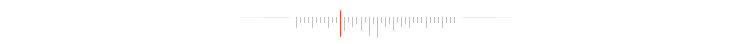
我在北京送快递
文|胡安焉
高楼金总共有16栋楼,其中1号楼到7号楼住的是回迁村民,8号楼到16号楼是外来的租客。回迁楼的快件都很好送,他们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买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门边或水电井里。因为村民们彼此熟识,邻里间会互相关照,连贴小广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楼里的老人逮住。相对地,租客住的几栋楼就鱼龙混杂,他们大多是北漂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合租户,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没有人了。住户之间彼此不认识,楼里进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丢失。我刚到高楼金的时候,同组的一个同事就让我送8号楼到16号楼,他自己送1号楼到7号楼。于是我每天送半个高楼金、一个新城乐居,加影视城工地,三个分开的地方来回跑,经常疲于奔命、气急败坏。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我发现小区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刚来的时候,谁都是从最烂的小区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没走。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剩下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新人刚来时一般都不会太计较,但逐渐地就会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平。这种心态的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车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
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元。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车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丢件,但也有别的情况。当时高楼金有个韵达小哥,在小区里三轮车开得太快,避让一个孕妇时,车子侧翻摔倒,前挡风罩脱落碎裂。孕妇虽然没被撞到,但受了惊吓。他修车加赔偿人家花了近2000元,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了。
我还记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说“我已经不干了”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比那个孕妇小。我听说过的金额最大也最离奇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方恒东景小区。一个快递员在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水管或接头被他弄坏了,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元钱。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一般来说,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说客户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头表达谢意的时候——虽说那种时候我也很欣慰。
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我们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元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场行情。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流动到其他地区或其他工种。那么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元。这就是我的劳动价值——我避免用“身价”这个词。我每天工作11个小时,其中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总共花去一个小时,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来派件的9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反过来看,这就是我的时间成本。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如果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其中10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在派件的时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我花一分钟打个电话,除支出0.1元的话费外,还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我将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还要付0.4元,那么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将亏损更多——不仅打了电话,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这些还只是顺利的情况。假如电话没人接听,我将在等待中白白浪费一分钟,也就是0.5元。还有的电话打通后就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我满足不了的要求。有时打完一个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可这快件还在手上没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还是在玉兰湾,我在客户预约的时间上门取一件唯品会的退货,但客户并不在家。电话接通后,是一个亲切的中年女声,她说要晚上七点后才到家,让我到时再过来。不过七点后我已经下班了,所以我让她把预约时间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说,明天也是七点后到家,她每天都是这个时间。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您把退货带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诉我,她在医院上班,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处理私事。像这种情况,她只能自己把退货寄回了,唯品会的上门揽退不支持夜间预约。不过那样她会有点儿麻烦,因为玉兰湾的快递员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门收件。但S公司的运费远高于平台补偿的10元,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发S公司。而发其他快递,她要自己带去快递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费这个劲儿。相比而言,在电话里动员我是更省心的解决办法。何况她显然是个乐于沟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争取就有可能。
在我拒绝了她的几个提议后,她问我能不能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到玉兰湾散步,顺便把她的退货取了。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态度,措辞很得体,语调温婉,富有感染力,简直无可挑剔。不过,晚上到她的小区去并不像她说的那么诗情画意,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
或许她自己是个工作狂,义无反顾地愿意为工作付出和牺牲,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她认为我理应和她一样。可是我的觉悟没有达到她的水平,而且我还想反过来建议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饭出来散个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掉。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说,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她。后来我还给她送过几次货,面对面的时候她仍然很礼貌,丝毫没有因为我曾拒绝过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码没让我感觉出来。
(本文摘选自《我在北京送快递》,有删节)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