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3岁起,查尔斯·布考斯基便接触到了平生两大嗜好:写作与喝酒。作为一位异常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写了五千多首诗,出版有六部小说集、数百篇短篇故事,但直至50岁左右才真正名声大噪。阿尔贝·加缪称他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时代周刊》将其誉为“美国底层的桂冠诗人”。
由于布考斯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洛杉矶,他的作品受洛杉矶的社会环境影响很大。他擅长书写美国社会边缘穷苦人民的生活,无业游民、酒鬼和妓女都是他故事里最常出现的主人公。布考斯基本人同样穷困潦倒,唯有酒、女人、赛马和古典音乐不可或缺。为了谋生,他从事过五花八门的工作,诸如洗碗工、卡车司机、邮递员、门卫、加油站服务员、仓库管理员、电梯操作员等,与此同时,他也将生活中的卑微、肮脏,荒谬乃至疯狂,都酣畅淋漓地写入作品中。
1965年,当时还是办公用品经销商的约翰·马丁在一份地下刊物上看到了布考斯基的作品,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挖到了宝。他首先给布考斯基写信建立联系,并于次年成立了黑雀出版社(Black Sparrow Press),以供布考斯基全职写作。作为粉丝、挚友和文学经纪人,约翰·马丁在布考斯基人生最后的20多年间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成功地将一个地下作家推到了文学圈的聚光灯下。
然而,布考斯基的成功绝不是由于一时的幸运。尽管他35岁时才开始创作第一首诗,还曾数次被杂志社、出版社退稿,但在写作这件苦差事上,他比绝大多数人更勤奋、执着,也更甘之如饴。正如他在写给约翰·马丁的一封信中所言:“没有什么能比在纸上写出一行行句子,更有魔力、更美好。全部的美都在这里了。一切都在这里。任何奖赏也都没有写作本身更伟大,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近日,布考斯基的书信集《关于写作》中文版出版,收录了布考斯基写给出版人、编辑、朋友和作家同行们的近150封信。就大部分内容而言,这些书信都有明显的即时性,布考斯基很少说套话,总是在信中侃侃而谈,以满腔热情讨论着日常事件,坦率地分享他的创作洞见。对他而言,写作类似一种无药可救的愉快的疾病,而诗歌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他从始至终坚持创作一种清晰明了、从生活出发的诗歌,反复批评那些公认的伟大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都是陈词滥调、空洞无物。在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布考斯基最典型的特质:生猛、机智、动人、干脆利落、毫不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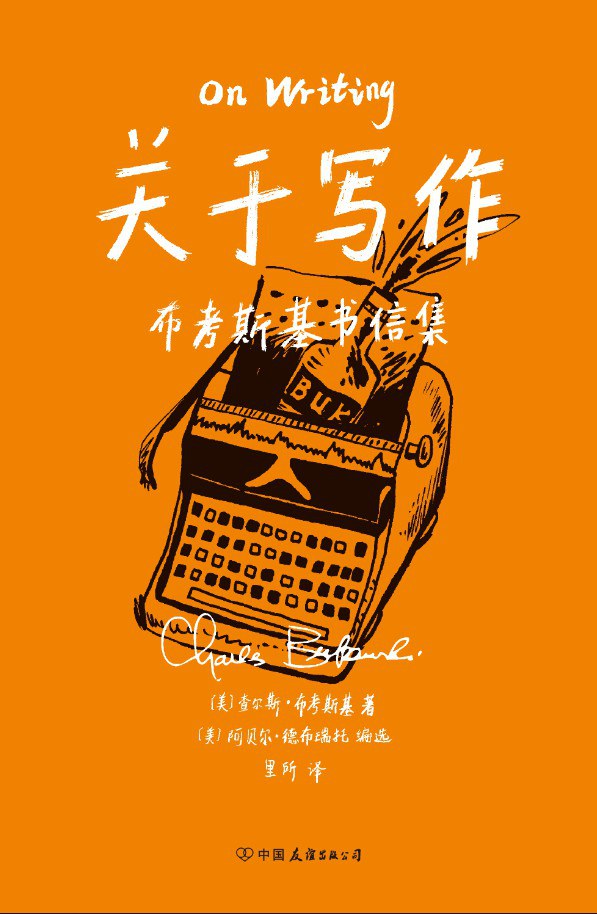
[美]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里所 译
磨铁图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1-04
致乔恩·韦伯(1961年1月底)
……当你为了要“作”一首诗而在诗中对自己说谎的时候,你就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会反复修改自己的诗,而是保留它们最初被写下的样子,因为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说谎,再怎么修改都救不回来,如果我没有说谎,嘿,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有时我读一些诗,总能察觉到它们是怎样被修剪、打磨、固定在一起的。你可以在现在的芝加哥《诗歌》上看到很多这样的诗。当你翻阅那一页页纸,空无一物,除了花拳绣腿,几乎都是没有生命的蛾子在乱飞。当我翻看这本杂志时,我真是被吓到了,因为那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猜这就是他们所以为的诗歌的样子,好像诗歌就应该是空无一物的东西。就是些精致分行排列的东西,太精致了以至于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诗歌完全被变成了智力艺术。滚去吧!唯一能体现一件好艺术品有智力的地方在于,它能让你被活生生地触动,否则就都是胡扯,你告诉我,芝加哥《诗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瞎胡扯的东西?
我第一次开始写诗是在1956年,当时我35岁,在长时间的上吐下泻之后,我已苍老无比,我确实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喝那么多威士忌了,因为有个女士声称我上周五晚上喝着波特酒在她那里蹒跚地走来走去——1956年我给《实验》寄去了一些诗,他们当时接受了,现在过了五年之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要发表其中的一首诗,他们的反应可真够慢的,但好歹终于有了回复。他们告诉我那首诗会于1961年7月被刊登出来,我想当我读到它的时候,会像是在读自己的墓志铭吧。然后她建议我汇给她10美金,这样就能加入他们的《实验》了,自然,我拒绝了。天哪!要是能在今天的中距离赛马中,我再押上10美金在“团结”(赛马的名字)身上,那可够我再爽一阵子的……
致乔恩·韦伯(1962年10月底)
(注:布考斯基被《局外人》的编辑评选为“年度局外人”,菲利克斯·斯蒂芬尼尔在一封信里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下面这封信则是布考斯基在对菲利克斯·斯蒂芬尼尔的回应。)
……关于斯蒂芬尼尔:像菲利克斯这样的人应该经常什么都搞不明白。至于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很多概念和前概念,多半他们还停留在19世纪。如果一首诗看上去不像拜伦勋爵那种调调,那你就只是写了一堆如床上的饼干屑般破碎的文字而已。政治家们和各个报纸大谈特谈着关于自由的言论,可一旦你真的试图得到自由——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形式上——你却被关进了牢房,面对着嘲讽和误解。有时当我把一张白纸放进打字机里,我常想……你很快会死去,我们都会很快死去的。这么说死去可能不是什么太坏的事,但既然你还活着,你最好按照深藏你内部的秉性活着。可要是你足够诚实,你可能早已在醉汉监禁室了结过15或20次啦,你可能失去了几份工作、一两个老婆,你可能在街上把某个人重击在地,时不时地只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要是你开始写诗,你无须担心自己写得像不像济慈、斯温伯思、雪莱,你也不用像弗罗斯特那般行事。你不用担心扬扬格、字数和结尾要不要押韵。你只想写下它,猛烈地,粗鲁地或用其他方式——任何你能真正写出自己的方式。我可不认为这意味着我“在左外场寻欢作乐”……扯着我最大的嗓门,“舞动着双手在表演”,我可没有像斯蒂芬尼尔先生提到的那样,“挥舞着他的诗像挥舞一面旗子”。由此可以推断有些人不惜任何代价地想获得广为人知的感觉;由此可以推断坏艺术只是为了追逐名声;由此可以推断有些人是在表演和招摇撞骗。不过这些罪名在所有的艺术领域早已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并且它们现在继续在绘画、音乐、雕塑和小说领域肆虐。大众,普通大众和艺术大众(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仅仅是些练习生)永远都是滞后的,不论是在物质和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所谓的精神生活方面,他们总想过得安全一点。假如你在12月戴着一顶草帽,你就蠢死了。假如你写的诗脱离了19世纪那种老套柔软的韵诗的巨大催眠术,他们就会认为你写得差极了,仅仅因为你的诗听起来就不对。他们只愿意听见他们经常听见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每个世纪里,都会有五六个非凡的人物要把艺术和文学从陈腐和死亡之中拽出来,再把它们向前推进。我并不是说我就位列那五六个人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属于他们之外的其他人群。正因如此,我被悬身局外。
好吧,乔恩,我想说如果你找到版面,就把斯蒂芬尼尔说的那些话发出来,那也是种观点。我倒宁愿被描述成一个砌砖匠或拳击手,而不是一个诗人。所以这一切也没什么不好的。
致威廉·帕卡德(1972年10月13日)
关于诗歌写作,我们还是应该玩得轻松点。很高兴我还能写点散文,还能喝酒,还能为了终止痛苦而和女人做斗争。我接受了一些关于诗歌技艺的采访,我感觉那些人都是被打磨好的红木。我猜那是因为他们学习得太多而生活得太少。海明威用力在生活,但他后来也被锁在了技艺里,很快技艺就变成了他的牢笼并杀死了他。我猜测这大约都是我们怎么选择自己道路的问题,这都是当我们还是孩子时迷失在一处码头上的写照。迷失是很容易的,迷失。当然我也并非要站在什么制高点上说这些。让我们为幸运喝一杯,同时怀揣着女人们依然会爱我们衰老灵魂和干枯大腿的希望。哦,如何写诗,该死!
附上更多我的诗。我正试着建造一个诗库,我要用我的诗歌炸毁这个世界。是的!

致威廉·帕卡德(1984年5月19日)
好的,既然你问了……否则,讨论诗歌或缺少了诗歌会怎么样,真的有点太过“酸葡萄”——关于水果不好吃的老套表达。这真是蹩脚的开场白,不过我只喝了一口酒。老尼采看得很准,当他们问他(也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了)关于诗人的问题,“诗人?”他说,“诗人们说了太多谎话。”这只是他们所有错误中的一个,假如我们想知道诗人们到底怎么了或现代诗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需要回头看看过去。你知道,现在学校里的男孩们都不喜欢读诗,甚至还要取笑诗歌,将诗歌看低为某种娘娘腔的运动,他们这是彻底错了。当然这里面有一种长期积累的语义学转变,使得读者很难全神贯注地去读诗,但这还不是让男孩们放弃诗歌的最主要原因。诗歌本身就出了问题,它是假的,它没法触动任何人。拿莎士比亚举例:读他的东西简直令你抓狂。他只是偶尔能点中要害,他给你一个闪亮的镜头,然后又回到不痛不痒的状态直到下一个要害出现。他们喂给我们的诗人都很不朽,但他们既没有危险性也不好玩,我们就会把他们丢到一边,去找些更正经的事情做:放学后打架打到鼻子流血。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不能尽早进入年轻人的意识里,最终你只能见鬼去吧。爱国者和信仰上帝的人都非常明白这一点。诗歌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一点,并且看起来未来依然做不到。是的,是,我知道,李白和别的一些中国古代的诗人可以只用几行简单的句子,就表达出一种伟大的情绪和伟大的真实。当然,也有例外,尽管还没能跨越更多的阶梯,人类也并非一直都是残废的。但大量的纸书印刷品和与之相关的东西都非常不可靠,都空洞无比,几乎都像某个家伙对我们做的恶作剧,或者比这还要糟糕:很多图书馆都是笑话。
现代借鉴过去,并延续了过去的错误。有人声称诗歌是写给少数人的,不是给大众看的。很多政府机构也是这样,还有那些富人、某个阶层的太太们,还有那些特别建盖的厕所。
最好的研读诗歌的方式是阅读它们然后忘记它们。如果一首诗无法被读懂,那我不会认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可取之处。很多诗人都在写一种被保护起来的生活,他们可写的东西非常有限。比起和诗人们聊天,我经常更愿意和清洁工、水管工或炸点心的厨师聊天,因为他们懂得更多关于生活的日常问题和日常欢乐。
诗歌可以是令人愉快的,诗歌可以写得清晰明了,我不理解为什么它非得被弄成别的样子,但它确实就成了那种样子。诗歌就像坐在一间闷热的、窗户关死的房间里,任何空气和光线透进来的可能都很少。很可能这个领域已经被从业者彻底败坏了。每个人都太容易把自己称作“诗人”。当你假定了自己的立场,你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大多数人不读诗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现有的诗都太差、太无力。难道精力充沛的创造者都去搞音乐、散文、绘画或雕塑了吗?至少在这些领域里时不时还有人能推翻陈腐的高墙……
致A.D.维南斯(1984年6月27日)
……我想对我来说最幸运的事情是成了一个作家。50岁之前我一直都不成功,不得不四处谋生。这让我得以远离其他作家和他们的社交游戏,并且远离他们的中伤和抱怨,既然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些运气,我依然会让自己离他们远一点。
他们继续他们的攻击好了,我只想继续我的写作。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寻求不朽或什么名声。我这么做因为我必须去写和我想写。大部分时间,我感觉都挺好的,特别是每当我坐在这台机器前,词语不停涌出,并且好像语感真的越来越好了。不管这是真是假,不管这么做是对或错,我会一直写下去。
致亨利·休斯(1990年9月13日)
(注:1990年1月,亨利·休斯在《梧桐评论》上发表了布考斯基的诗。)
很高兴我有几首诗被你选中了。
我现在70岁了,只要红酒还在流,打字机还在响,就都没问题。当我为了房租给那些男性杂志写黄色故事时,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精彩的秀,现在它依然很精彩——我边写作边对抗着各种蝇头小利的危害,对抗着“终结”这个标牌邻近的脚步。有时我很享受这种和生活的辩论,换句话说,离开时我也将毫无遗憾。
有时我把写作称为一种疾病。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开心这种病找上了我。每当走进这个房间,看着这台打字机,我总能感觉到某些来自别处的事物,某些奇异的神灵,某种完全难以形容的事情,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絮絮叨叨的、绝妙的幸运触动着我,并且这幸运的感觉在持续、持续、持续。哦,是的!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关于写作:布考斯基书信集》一书,较原文有删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