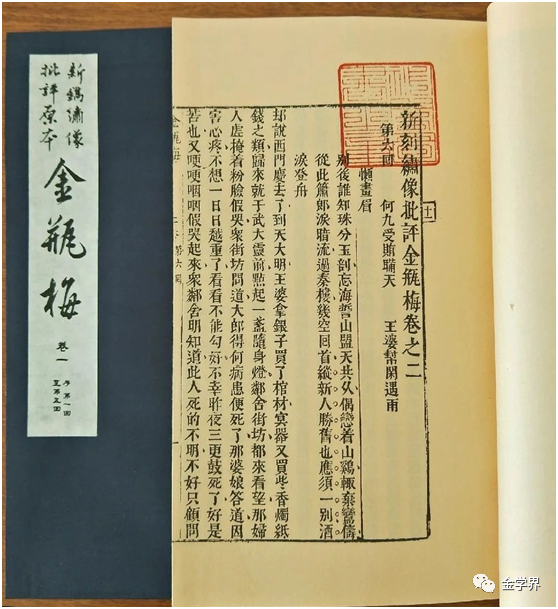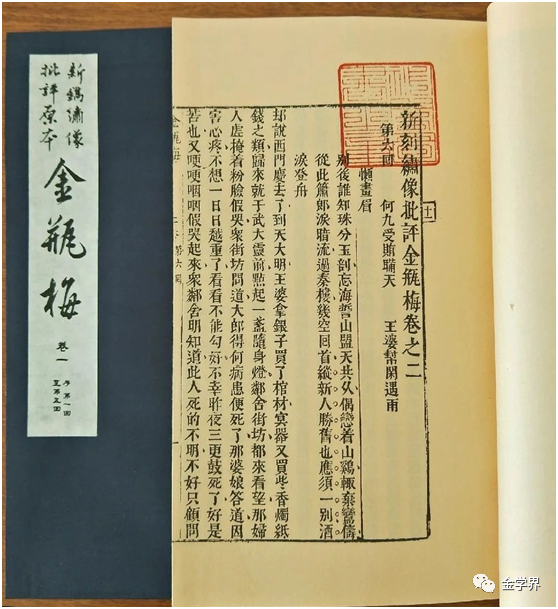文龙的《金瓶梅》批评和张竹坡的评点并列于《第一奇书》本上,二者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文龙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各类人物形象进行了比较深人的研究,表现出他敏锐的眼光,其中包含许多超出张竹坡的见解,具有独立的价值。
在文龙看来,笑笑生在塑造人物时“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于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是在明眼人之识之而已”。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其实,金圣叹在评论《水浒传》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而文龙用了更加清晰、更加理性的语言来表达,发展了金圣叹关于人物描写的理论。
文龙的人物论把作为普通人的典型的问题放在了很突出的位置,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金瓶梅》里一些重要人物其实只是普通人的典型,他们的行为也只是普通人的行为,并无什么奇闻异事。
他在分析西门庆这个人物时这样说:“吾谓人皆可以为西门庆。”虽然不过寥寥十个字,却是极为精辟的见解。
他指出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西门庆,为不会看书的人指点了迷津,使读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人物的份量。
他还在第一回的回评中说,一般人之所以没有成为西门庆,“大抵为父母之所管,亲友之所阻,诗书之所劝,刑法之所临,而其心未必不作非非之想也”。
“假令无父母、无兄弟,有银钱,有气力,有功夫,无学问,内无劝戒之妻,外有引诱之友,潘金莲有挑帘之事,李瓶儿为隔墙之娇,其不为西门庆也盖亦罕。”
这就是说,如果其他人也处在和西门庆相似或相同的地位,具有同样的条件,就必然会做出西门庆现在所做出的那些事。

《金瓶梅词话》
他对作为普通人典型的西门庆的市井小人特征洞若观火。
在第四十一回回评中,针对西门庆对定亲一事的态度,文龙评道:“西门庆直现于声色,左曰不般配,右曰不雅相。此刻之西门庆,又非复当年之西门庆矣。小人得志,大抵如斯。”
他指出西门庆这一席话正是一个暴富的市井小人的典型表现,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而文龙对普通人的人性特征却认识不足。
比如针对西门庆对应伯爵这些帮闲的周济施恩举动,他认为就好比是“修庙、印经”者的伪善举动。
其实,这些行为只是出于西门庆散漫使钱的习性,以及他一息尚存的朋友义气。
文龙对这件事情上的局限,有可能是受到以往小说人物类型化的影响,难以摆脱过去小说风格夸张、人物性格单一的影子,所以在评价人物时他虽然看到小说表现的是普通人,却不能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这种观点的价值。
其实,正因为西门庆是个普通人,他的行为才如此难以界定。也唯其如此,这个人物才如此吸引人,如此富于魅力,表现出一个成功艺术形象的无限神韵。
因为意识到《金瓶梅》描绘的是普通人的悲喜剧,所以文龙在看到第二回潘金莲与西门庆相勾搭时这样说:“吾尝疑男女苟合之太易,吾今知男女苟合之不难也。”
他看到《金瓶梅》塑造的是普通人的典型,看到了这些人物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因此他的评点常常把笔触深人到现实社会,指出书中内容是现实世界的普遍反映。
在讲到潘金莲时,他说,“若潘金莲者,处处有之,吾亦时时见之。虽人告我曰:此不姓潘,此不名金莲。予语之日:潘金莲,亦不必实有其人也。……第恐事同金莲之事,心同金莲之心,纵无其事,并无其心,而淫与金莲等同,虽不名金莲,直谓之姓潘可也。”他认为,像潘金莲这样的淫妇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有之”,
潘金莲正是生活中许多相似或相同人物的艺术化的代表,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总之,在文龙的眼里,“《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这样解释道:“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
文龙在评点《金瓶梅》人物时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他在评价西门庆与陈敬济时说:“此翁婿二人,均不过一鸟物而已。”此处的用语虽然尖刻,却是十分准确的。
因此,由这两个人物贯串起来的故事是一出人间喜剧,他们是被“笑”的主要人物,读者应当怀着“笑”的心态来看这部书,由此获得对这部书的准确理解。
可见,这个评价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作者塑造这两个人物的本意,对读者理解人物及欣赏全书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他在第三十五回回评中评价西门庆说:“外貌似有才能,其实半生尽为人之所使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西门庆既可笑又可悲的本质。
又如第五回针对武大这个形象评道:“甚矣,人之不可有所恃也,而无能者,尤不可有所恃。……若武大郎何所恃乎?才不能以倚马,力不能以缚鸡,貌不足以惊人,钱不足以使鬼,所恃唯一好兄弟耳,固非其所自有者也。呼之不能即来,望之不能即见。而彼之所恃者,又为人之所畏,一露其机,于是有死之路,无生之门矣,岂不痛哉!”
一般人都认为武大郎之死纯属无辜,而文龙认为武大郎本人也负有部分责任,他没有采用恰当的方法来处理老婆与别人勾搭的事,而是极为冒失地以兄弟武松相威胁,致使对手对他下毒手。
文龙认为“无能者,尤不可有所恃”,否则就是取祸之道,这样的思想在众多关于武大郎的评论中,表现了他分析人物形象时独到、深刻的眼光。
当然,文龙对《金瓶梅》人物的分析评价也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封建土大夫文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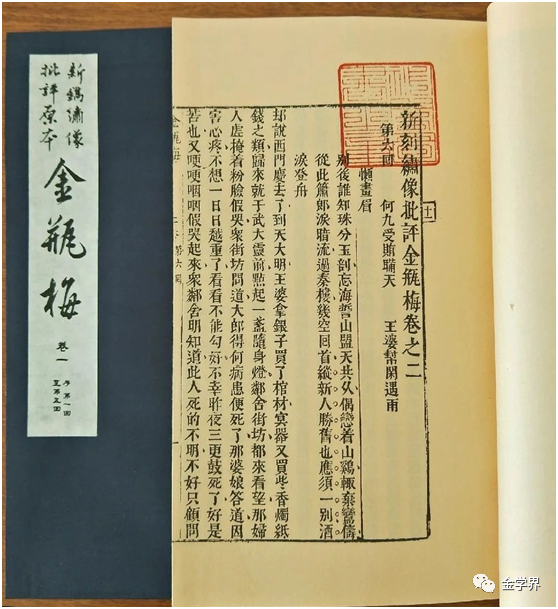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影
有意思的是,在对待孟玉楼与吴月娘这两个人物的问题上,文龙与张竹坡的见解截然相反。
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观点与作者相同,一个激赏玉楼而批驳吴月娘,另一个则持相反的态度。
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各有偏颇,也各有合理因素。吴月娘与孟玉楼都是作者较为肯定的人物,都是作为较有妇德的女性出现在作品中的。
张竹坡不满吴月娘的理由是她没有阻止丈夫西门庆胡行妄为。
对此,文龙在第十二回批评道:“西门庆之粗鄙不堪、凶顽无比、无情无理、糊里糊涂、任性纵情、恃财溺色……可见为之妻妾者,直与猪狗同眠,豺狼共食。……为之妻者,将如此良人何也?”
他认为张竹坡对吴月娘过于苛求了,月娘与西门庆这么凶顽的人生活在一起简直就是与猪狗为伴,还能要求她去感化这样愚顽的丈夫吗?
文龙这种认识很有见地,也是很合理的。而文龙对月娘的赞赏主要还在于她遵守了封建伦理道德。
他在第十八回回评中说:“观人亦需论其大处,妇人之所最重要者,节。西门死后,月娘独能守,较之一群再醮货何如乎?赞美妇女者,但有从一而终,守贞不二之语,则以前所有处分,皆可悉予开复矣。妇人之所最忌者,妒。西门生前,月娘独能容。”
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了文龙的封建礼教思想。在他的眼里,女性只要能做到从一而终,守贞不二,则其他的缺点就都不在话下,都可以赦免了。
这种把封建伦理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的看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在孟玉楼的问题上,文龙虽然也承认她“诚不愧为佳人”,然而又一再指责她的不是对她极为不满。
在第七回回评中他批评孟玉楼“有财如此,有貌如此,人皆仰而望之。乃一见一个白净小伙,便以终生相许,虽非蠢妇人,亦是丑妇人,作者何取乎而以之自况也?”
认为盂玉楼以如此身份样貌而作出如此轻率的举动是既愚蠢又丑陋的,这样一个愚痴的女人怎会是作者用以自况的人呢?“作者何取乎而以之自况也”,是指张竹坡原评:“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
文龙认为孟玉楼的行为是出于“急色”,他说“妇人急色若斯,便非良善。”然而在第七十五回回评中他又评论玉楼:“若玉楼者,却是因情而不合,因情而大吐,因情而致西门庆之来。乃西门庆仍是以淫报答之,此玉楼之所以终不能常守在西门庆家也。”
为何会出现这样既意识到她的优点又对她求全责备的矛盾的评价呢?
我们可以在第二十九回回评中找到答案:“天下岂有一嫁再嫁,犹称为贤良之妇哉?”
脑子里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的文龙在妇女问题上是极为保守的,在他看来,一个女子一嫁再嫁就称不上贤良了,有了这样的过失,纵然有再多的优点也是枉然,也算不上是一个好女人了。
即使是西门庆这种凶顽之人的女人也必须守节,否则就是“再醮货”,文龙这观点当然是极为迂腐的。
当然,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似乎不能在这一点上对他有更高要求了。

影视剧照 · 孟玉楼
孟玉楼不是个完人,文龙对孟玉楼的有些批评也很有道理。
如第二十六回回评中他指责孟玉楼:“背后一而再,再而三:‘大姐姐又不管’,分明指使金莲出谋,而暗中参议。”
指出孟玉楼在宋蕙莲一事上利用潘金莲激化矛盾,这种认识是有眼光的。孟玉楼此时心怀嫉妒,出于这样的心理她就狡猾地把潘金莲当枪使,表现出这个深心人的存身之术,这的确是她令人生畏之处。
不过文龙因此而批评孟玉楼是“老奸之辣货”,则又说得过火了些。
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嫉妒对一个女人来说本来就是要不得的,更何况她还采取了“阴险”的行动呢!
文龙在理性上时时处处批评孟玉楼,而在感情上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孟玉楼的欣赏。
如第七回评说到玉楼过门后的情景时,他这样说道:“若写得太重,便失玉楼性情;若写得太轻,又非当时景况。故但以三日后‘来往不绝’含糊了之。”不可太重,亦不可太轻,这分明是对孟玉楼美人性情的欣赏。
文龙本人对自己的这种倾向似乎并没有很明晰的认识,客观上则为我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评论,给我们以审美心智方面的启发。
从这一点上来看,文龙对孟玉楼的评点还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不比张竹坡在吴月娘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态度。
在谈到宋蕙莲的时候,他流露出很强烈的封建男权思想。
圣人谓其难养,近之远之皆不可……又有小人而女子者,阉宦是也。女子而小人者,婢妓与仆妇是也。其性属阴,其质多柔,其体多浮,其量隘,其识浅,同是口眼耳鼻,别具肝肠肺腑,令人可恨,兼令人可哂。善读书者,于此回之蕙莲,其光景情形,详细玩味,便可触类旁通,则所以待女子小人者,思过半矣。” 其性阴,其质柔,其体浮,其量隘,其识浅……这些蔑视女子的话充满了头巾气、迂腐气,包含浓厚的封建色彩,是文龙评点中的遗憾之处,也是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所导致。
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因此他对宋蕙莲的轻狂感到不能忍受,看不到她身上的闪光点,对她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仅仅把她看成一个十足下贱的女人。
第二十四回回评中他说:“此回写蕙莲轻浮之态,可谓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世间有此等贱货笨货,而且颇多,一误纵之,便思上天,如断线之风筝;一误触之,使人握耳,如燃捻之爆竹。彼绝不知人有羞耻事,此时虽欲收服之,不可得也。”
把宋蕙莲说得一无是处,全然无视她最后以死相抗争的悲壮色彩,也看不到她作为受害者和牺牲品的悲剧性质。

戴敦邦绘· 宋惠莲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描写了西门庆与林太太荒淫的情景,对此他批评道:“此回令人不愿看,不忍看,且不好看,不耐看,真可不必看。此作者之过也。”
在他看来,只有像潘金莲、宋蕙莲那样的下等女人才会有那些不堪之举,而林太太这样的贵族妇女竟然也投入了市井小人的怀抱,这岂不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大讽刺吗?岂不是颠覆了他的一贯信仰?
他认为展示这样的场景是“作者之过”。殊不知作者恰恰是要通过林太太的事来讽刺封建贵族阶级,以达到他“骂尽诸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