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死亡、一个人的村庄
汤圆的圆2020-11-05 13:01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全国人民喜气洋洋,每个人都守着电视看直播,为了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场景拍手叫好。这几乎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时代回忆。
但几乎,并不是全部。在我们欢欣鼓舞的时候,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我们的记忆并不相通,他们,被时代忘在了身后。
“你知道 2008 年奥运会在哪里举办的吗?”
“不知道。”
“你知道天安门在哪里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哪儿吗?”
“不知道。”

镜头记录下的这组对话,发生在导演蒋能杰和几个农村留守儿童之间。那是在 2011 年,蒋能杰在光安村拍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的第二个年头。
他始终记得那次采访,孩子们只回答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主席是谁吗?”
“知道啊,是毛主席。”

回答的时候孩子们终于挺起了胸膛,在这之前他们因为回答不出那些问题害羞地低下了头。
蒋能杰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错位感——
大山外,和大山里,我们,和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01
2009 年,导演蒋能杰首次走进村小,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间临时学校和 22 个学生的日常点滴。
孩子们的一天从凌晨四五点就开始了。
为了上学,他们每天必须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走上十几公里的山路,天亮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就能赶到学校了。
山路崎岖,孩子们通常结伴而行,姐姐带着弟弟,哥哥拉着妹妹。

只有 6 岁的蒋云洁不同,因为家住在最深的山坳里,家里又只有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小云洁每天只能一个人上学,一个人爬山路,摔倒之后再一个人爬起来。
第一次摔进泥水坑里那天,她回到家向奶奶撒娇,说今天不小心摔了一跤,好痛。奶奶听了之后对她说,女孩子家家读书也没有,又这么危险,干脆不要念了。
从那之后,小云洁无论摔得多痛,都不会再和奶奶说了。
因为她想读书。
有时候衣服被泥巴蹭的实在脏,就撒个谎说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不小心弄的。
大家都知道,村小没有操场,教室门前那块稍微平坦一点的泥巴地就是孩子们活动玩耍的场所。

第一次在光明小学见到小云洁的时候,蒋能杰就记住了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小姑娘。别人读课文的时候偷偷摸摸开小差,她永远把书本树得笔直,眼睛一刻也不离开。
都不用说,就能从她的脸上,她的眼神里看见对念书的渴望。
这让蒋能杰有些激动又有些好奇,激动是因为他欣慰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好奇是因为她才这么小,怎么能懂这些?
下课之后,蒋能杰问她:“你很喜欢念书吗?”小云洁回答他:“对,我想读书。”
“读书干什么呢?”——走出大山,改变命运,几乎不用想蒋能杰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个完美答案,他知道留守儿童的励志故事会是纪录片最催泪的素材。
但,
“读书,然后像爸爸妈妈一样,去打工。”
蒋能杰懵了。

之后的两天里,他又随机采访了几个孩子,答案出奇地一致:去打工。
将来最想做什么?——去打工。

这是他第一次 ,如此明显地感觉到大山里,和大山外,那种剧烈的错位感——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畅享未来,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做设计师,有人甚至梦想成为航天员。
而他们像野草一样,在山里扎根生长起来,从没看过外面的世界,也想象不到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剩菜冷饭里明白了“穷”的含义。
关于未来,最好最好的样子,好像就是像爸爸妈妈那样,去打工,去赚钱,去努力让自己不那么穷,那么苦。
蒋能杰开始明白,对于这个大山里的世界而言,最可悲的不是没法选择,而是无从知晓。
02
在光安村呆得越久,蒋能杰感到越无力。
他看着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读着五星红旗我在你的光辉里里你在我的心窝里,念着妈妈是家里的月亮妈妈是家里的太阳,讲着中国人都是好人日本人都是坏人......
却不知道首都是北京以为当今领导人叫毛主席,却爱骗不识字的爷爷奶奶说作业做完了,却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笑着说:圆的。

现在,他们连这样唯一的读书机会都要没有了。
县里下达了指令,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要开始集中办学,光明小学要被拆了,孩子们要被送到县城的学校继续读书。
这根本不现实。
因为县城的学校条件也有限,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宿舍,孩子想要送到县里继续读书,也就意味着家长必须跟着,租一间屋子陪读。
“一年几百块的房租,我们根本付不起,好心人给捐了校车,也没用,山里的泥巴路太小,根本开不进。”
看着村小的老屋被推平,村长急得不行,对着蒋能杰的镜头他几乎要哭出来。

村长急,蒋能杰也急,村里的老人们看着村长急也跟着急。
唯一不着急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蒋恒和蒋鑫两兄弟甚至有点开心,因为学校没有了,就不用读书了。
以前蒋鑫还要经常苦恼用什么样的借口骗老师,把自己没做作业的事糊弄过去。现在可好了,学校没有了,老师的念叨没有了,天天跟着哥哥满山坡去玩。
就连蒋云洁也不怎么着急了。
想读书是因为妈妈说了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找得到好工作。而最近一个同学告诉她,你不读书,将来也能去打工。
在她小小的脑袋里,妈妈说的“好工作”就是打工。
而村小的大部分孩子都不愿意读书,他们大多抱着同样的想法:长大了就去广东,像父母一样去打工。

而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要用功读书,以后不会像他们这样卑微辛苦地活着。
可怕的是,孩子希望像父母那样生活,因为他们能看得见想得到的,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去打工。
可悲的是,父母并不知道孩子的希望,他们还沉浸在自我的美好的想象中,把孩子的未来当做支撑自己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唯一动力。
每当蒋能杰听到这些父母打电话回家,要孩子努力,要孩子刻苦,满心期待地询问成绩的时候,他再一次越发地感觉到了大山外和大山里的错位——
大山外父母们沉甸甸的期望,大山里孩子们给自己框死的未来,
互相矛盾互相割裂,在冰冷的现实面前逐渐走入死路。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03
村小没了,蒋能杰以为也就到这里了。
但并没有。
一年之后,他再次回到光安村,原来老校舍的位置上起了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晚上他找到村长,村长告诉他,几个月前光明小学重建,最近刚刚建好。
蒋能杰参加了新村小的剪彩仪式。
“在市里县里各位领导的支持和努力下,光安村光明小学终于重建成功了,我很高兴,这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蒋能杰忽然就想起了那天晚上,村长对他:
“小杰啊,我和你说心里话,我真的好难,好难。我去了乡里县里市里,我反映说光安村的学校必须重建,不建不行,最后他们说修,没修,说要修又没修......”
村长话没说完,蒋能杰却已经明白了眼前这个古稀老人哽咽背后的全部苦涩。
那是属于光安村所有人,属于大山深处所有人只能咽下的无奈和心酸。
当初那种强烈的错位感再次袭来——
这次,更多了一些不可说。那些漂亮的场面话和那晚老村长的心里话,在他脑海里不断交替出现,蒋能杰有些难过。
他希望这一次回来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想给纪录片再取一个“别名”,就叫“希望!希望!”
这个“别名”,也是他最希望给范魏媛和范魏煜姐弟说的一句话。
七年前,姐弟俩的妈妈在生弟弟时难产去世了,父亲顶不住生活的压力,在广东抢劫进了监狱。

他们跟着奶奶生活,奶奶前不久被查出得了乳腺癌,晚期。
而他们连一盒药都买不起。
绝望。
不是某个时刻,而是塞满了生活里的每一天。
范魏媛常常在深夜躲在被子憋着声音哭,哭一会儿就停,因为她还要赶在天亮之前收拾好自己红肿的眼睛,不敢让奶奶和弟弟看出来。
她每个月都会给爸爸写信,然后再从回信里捡那些好的内容读给奶奶和弟弟听。
对范魏媛来说,对家的守望,就是她能抓住的生活里唯一的那一簇光。
她告诉蒋能杰说她已经打算好了,等初中读完就不读了,去挣钱供弟弟继续读。她还说,她会等爸爸,等他回家,等他团圆。
摄像机的镜头关掉之后,蒋能杰听到她很小声地说了最后一句:“这一天快一点到来吧,奶奶的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他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在心里默默许下:希望!希望!
04
2014 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村里来了一队志愿者,他们给村小的孩子带来了很多物资援助。离开的时候,还安排了蒋恒蒋鑫兄弟和父母视频通话。
兄弟俩显得有些局促,他们呆呆地看着听着,被一群自愿者围在屋子中间,快一年没见,屏幕那头父母的脸有些陌生。
偶尔点头应一句“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听父母说,那些分量很重的话,我并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
结束的时候,有人从后面碰了一下蒋恒,然后他捏着手指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对父母说了一句:“我爱你。”

满屋子的志愿者都哭得稀里哗啦。
很违和。
那种挤得满满当当的热闹,其实并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常年空旷的村子里。
关于这段,导演蒋能杰在一个采访是这样说的:
“这件事算是个意外的,我们不知道志愿者要来,本来没打算剪进正片,但最后看素材的时候,我后悔了。我觉得需要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看看,不是看温馨,而是看无所适从。”
孩子们的无所适从。
我忽然就明白了导演把这个场景用作纪录片结尾的用意。无关爱心和善意,我们其实永远都不应该擅自去揣测他们,也不需要理所当然地“教会”他们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着父母说一句“我爱你”。
毕竟这些孩子平时都习惯了拿着小时候的相片,想象父母现在是什么样子。

春节终于到了,孩子们的父母都回到了光安村,电视里春晚主持人倒数的声音和外头的鞭炮声同时响起,空旷了一年的村子再次热闹起来。
蒋云洁再也不用抱着相片努力想象妈妈的样子,
蒋恒蒋鑫听着父母没完没了的唠叨也很开心,
范魏媛正在给爸爸写信,她说弟弟这次又考了第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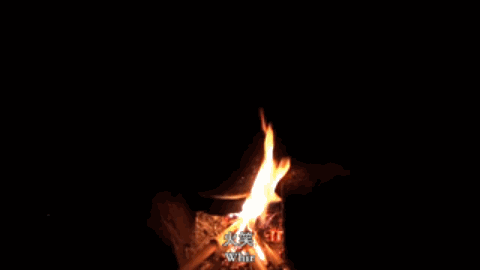
片刻的团聚过后,
这些孩子继续怀着长大要去打工的梦想,
在这片大山深处,
慢慢地长大。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