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不太确定那是蘑菇,还以为是地上的一张蓝色糖纸。它真的好蓝好蓝啊!
青春深圳2020-09-11 21:15

Stephen Axford,澳大利亚蘑菇摄影师。
拍蘑菇成为了我的一大热爱,完全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32:26
真菌如何改变了我眼中的世界
你好。非常感谢一席邀请我和远在中国的你们聊天,虽然只是通过视频的形式。
我叫Stephen Axford,是个蘑菇摄影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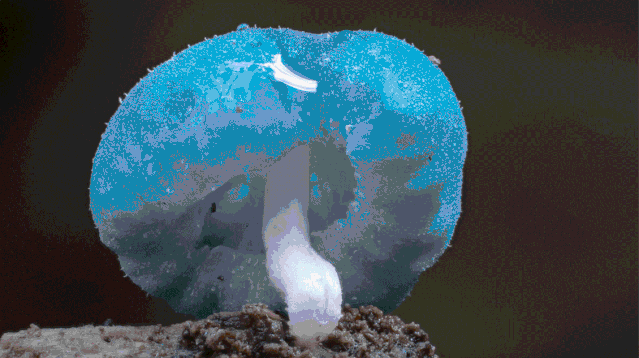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家附近的一片濒危的低地亚热带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岸。

过去十年里,我在这片林子里拍摄了许多蘑菇的照片。除此之外,我还去到地球最偏远的一些森林中拍蘑菇。拍蘑菇已经成为了我的一大热爱,完全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这是我拍的第一个蘑菇。它的学名是Cortinarius archeri。

▲ Cortinarius archeri,丝膜菌属
我为什么会拍它呢?
那还是2003年,我妻子因为乳腺癌在五年前去世了。我也得了可能会危及生命的病。
这两件事我都熬过来了。但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重新思考生命。我当时想重新塑造我自己。澳大利亚沿海的荒野和古老的森林便成了我的避难所。

有一天我沿着海边的小路散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紫色蘑菇。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紫色的蘑菇。要是你问我蘑菇是什么,我可能会告诉你它不是一种植物,仅此而已。
我当时还在做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从来没学过植物学和动物学,也不了解任何一门生命科学。但在我拍了这个蘑菇之后,我对真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森林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不再向上看,而是向下看,搜寻地上藏有的奇珍异宝。

这些是我早期发现的几种蘑菇。那个时候我特别注重色彩。
这是明绿湿伞,一种生长在塔斯马尼亚雨林里的特别漂亮的绿色蘑菇。

它相当小。菌盖只有1-3厘米宽。我发现这个标本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它们非常不容易看到——苔藓绿的蘑菇长在绿色的苔藓里。
我蹲下来拍照,以为拍下来的是非常特别的单一标本。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刚刚我一直跪在一整片藏在绿色苔藓里的绿色蘑菇上。

▲ 长在绿色苔藓上的明绿湿伞
这是红菇属。

通常外观看上去都非常完美。这种菌有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下面的白色菌褶鲜艳极了。

▲ 红菇属
它们对于摄影师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很多都是可以食用的。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有些根本不能吃。
这是我最喜欢的蘑菇之一。它叫炫蓝小菇。

通常会在四五月份出现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很多森林的落木上。
漂亮吧?

▲ 炫蓝小菇
所有这些种类都是人们一般想到蘑菇的时候会想到的。它们都有一个菌柄、一个菌盖,还有菌褶。但之后我发现的一些蘑菇一点也不像蘑菇,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什么是蘑菇”的认识太狭隘了。
比如这种橘色的真菌,是一种枝瑚菌属。

它们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颜色。看上去像不像海底的珊瑚?

▲ 枝瑚菌属
这些蘑菇成功吸引了我这个摄影师。
这是我开始看到的众多多孔菌之一,云芝栓孔菌。

▲ 云芝栓孔菌
这种真菌会存活很长时间。它们分解倒下的巨大原木和树桩。所以即便是其他蘑菇都不在了,它们也会生长。
这是叶状耳盘菌。是一种子囊菌,俗称杯状菌。

▲ 叶状耳盘菌
我从来都不知道真菌还有这么美的黑色。
顺便说一句,我听说这种菌类毒性极强。所以千万不要被它漂亮的外表欺骗了。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种菌。它叫珊瑚状猴头菌。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珊瑚齿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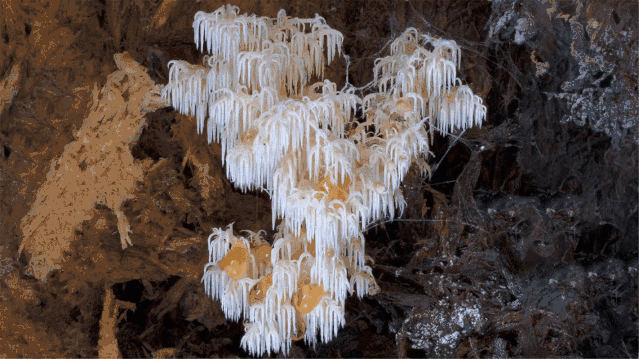
▲ 珊瑚状猴头菌
我们在云南的森林里看见了这种菌类。当地人告诉我们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
随着我开始发现这些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真菌,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意识到,蘑菇不仅仅是五颜六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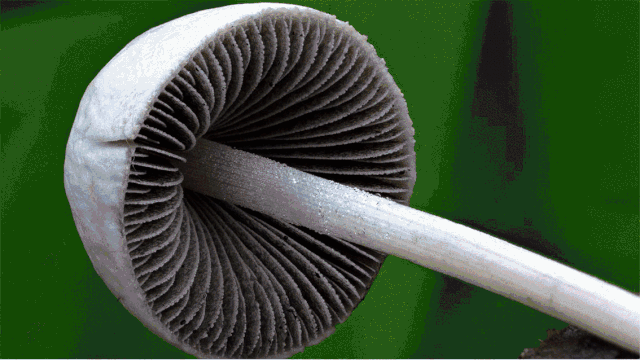
以摄影开启的旅程,后来变成了通过摄影这种工具探索菌类学的旅程。
我第一个大的发现就是:真菌并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而是一个完整且独立的生命王国。
科学家认为,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存在四五百万种菌类。但迄今为止我们仅记录了其中的20万种左右。所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
我拍的照片一般都是蘑菇,大型真菌的子实体就好像树上的苹果一样。

有些是腐生生物。这些都是森林的回收者。

真菌的主体——菌丝体,由大量的分枝、线状菌丝组成,在枯木、树叶、或者土壤中生长,分解死去的植被。

没有这些腐生生物,森林中倒下的枯树就会层层堆起。就像3亿年前后的石炭纪一样,枯死的树经年累月被压成了煤层。当真菌进化到可以分解树木中的木质素,接着再分解树木自身的时候,石炭纪就结束了。真菌将所有养分回收至土壤,滋养树木。
我在森林里拍的另一类蘑菇,就是外生菌根真菌。
这些真菌和树木之间是共生关系。它们为树提供土壤里的水、矿物质和营养物。树又为真菌供给碳水化合物。

你或许对“木维网”有所耳闻——就是菌丝体通过庞大的网络,将森林中的所有树木连接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树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相互交流,或是提醒对方病虫害,或是在森林中互相扶持、滋养生长。
科学家刚刚才开始发现树木是怎样利用这一网络的。但我们知道的是,通过这个真菌网络连接起来的森林里的树,比森林外面那些独自生长的树更容易存活。
另一种我一直在森林里记录的很酷的真菌,就是寄生性真菌。

▲ 寄生性真菌
有些寄生在树上的真菌可能真的会把树杀死。有些则寄生在昆虫身上。

这些通常被称为冬虫夏草。我们主要是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云南发现了大量的冬虫夏草。

▲ 冬虫夏草
我们总能因为冬虫夏草兴奋不已,因为它们实在太难找到了。你会看见地面上长出了子实体,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橘色的子座。然后你就会啊哈一声——冬虫夏草!这是我在菌物王国中探索时最有趣的过程之一。
这是一种黏菌。

黏菌这种东西太迷人了。和其他生命形态相比,黏菌的原生质体和疟原虫、阿米巴变形虫的行为更加相似。它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字,比如“狗的呕吐物”、“狼的乳汁”。

▲ 黏菌
因为它看上去像真菌,所以往往会被误认为是真菌。
接下来是地衣。

据统计,地球的陆地表面有6%都覆盖着地衣。很神奇吧?



<< 地衣:左右滑动查看 >>
很多人都以为地衣是一种植物,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藻类或蓝藻与两三种、甚至三四种真菌共生的产物。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碳水化合物,真菌的作用则是提供地衣的结构体。每一种地衣都需要它的藻类和所有种类的真菌才能存活。



<< 地衣:左右滑动查看 >>
和地衣有关的事情都很复杂。所以我只能坚持不懈地拍下它们的美,然后把科学的部分留给更专业的人。
真菌王国里随处可见这样的酷炫科学。看看这个鸟巢菌。

▲ 鸟巢菌
我经常发现它们长在我家花园的护盖物上。所以它们是无根的,长在木头上。
这些蘑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传播孢子的方式。你能看到在这些“巢”里面有一个个小小的“蛋”,每一颗蛋实际上都是孢子包(小包),而巢则类似于泼水桶(包被)。

因此每当下雨的时候,雨滴会击中这个泼水桶,将孢子包从巢中溅出来。有时候孢子最远会被弹出三米开外。
通常孢子包上会附着一条细线,当它撞到灌木或低矮的植被时,那条线会缠绕在树枝或叶子上,将孢子包固定在地面上。那么当它打开并释放孢子的时候,孢子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风中散播。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繁殖方式。
我听说有的蘑菇会在黑暗中发光,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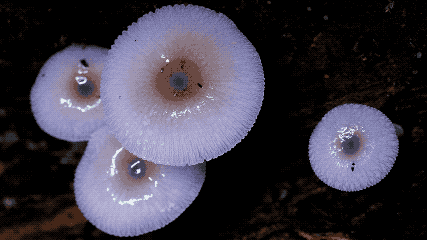
所以在一个下着雨、没有月亮的夏夜,我决定去我家后院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蘑菇。我在我家后院发现过许多菌类。
我关上了屋子的灯,走进小溪边的树丛中,然后关掉了我手中的手电筒。我本来准备等上几分钟,等眼睛能适应周围的黑暗。因为我之前见过的唯一发光的菌类,发出的光是很弱的。但我一关掉手电筒,它们就出现了——灌木丛中间闪着一颗颗小小的亮光!

我走过去,发现这些美丽的小蘑菇现出柔和的绿光。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那晚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快乐地流连其间。并拍摄了这些美丽的蘑菇——荧光小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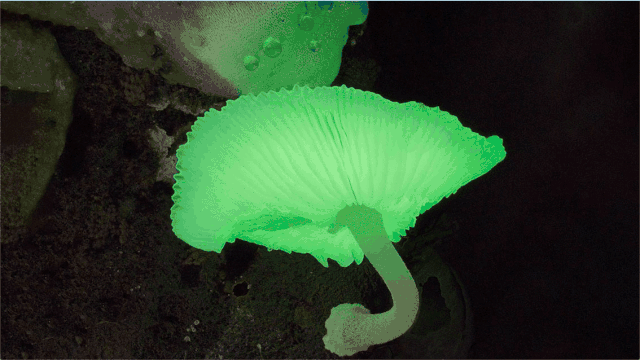
有时候这些蘑菇太亮了,只要拿上一根长满这种蘑菇的树枝,我就能在黑暗的森林小径中找到路。
找到这些蘑菇,为分享真菌的故事打开了不可思议的大门。它们是我第一次用延时摄影拍摄的蘑菇。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妻子支持我用腐烂的原木填充我们空出来的淋浴间,封上窗户,把那里变成一个延时摄影棚。那个时候Catherine(本片的拍摄者)还是影片的制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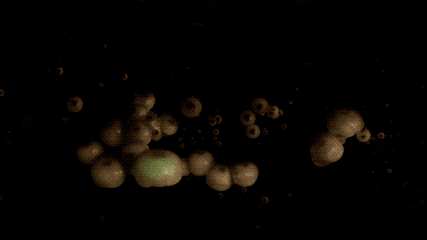
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的延时摄影变得越来越有野心。我成立了两个工作室,一个在棚屋里,一个在船运集装箱。
BBC在看到我创作的影片之后,爱上了它们。在《地球脉动 第二季》中,这些延时摄影作品和David Attenborough一起出现,被BBC评为《地球脉动》系列纪录片的前十。
00:58
从那时起,荧光小菇的延时摄影和许多其他种类的森林真菌,被收录进了另外十部国内外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中。

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真菌学家Tom May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说,这些延时摄影作品让真菌像猛犸象一样活了起来,这让普通人和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前所未见的东西。
澳大利亚的真菌学家屈指可数。对于他们来说,正好赶上蘑菇长出来的时候去到森林中也是很大的挑战。于是真菌学家们对我的摄影和延时摄影,能向他们展示怎样的真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我的角色也从单纯的真菌摄影师,转变成了自然学家和科学家们的合作者。
就像19世纪的自然学家一样,我有设备,有对自然界的热情,也有时间和机会去探索。我开始有了兴趣,不仅要捕捉蘑菇的美,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地捕捉蘑菇的形态和结构,与菌类学家的研究相得益彰。

我们发现的一些蘑菇实在太过与众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发现了新的物种。
这个蓝蘑菇就是。

我第一次发现它是在十年前,在离我家非常近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片森林。一开始我不太确定那是蘑菇,还以为是地上的一张蓝色糖纸。它真的好蓝好蓝啊!
我把样本寄给了Tom May博士,他认定这是一个新的物种,与新喀里多尼亚首次记录的标本相似。

▲ 新喀里多尼亚的leratiomyces atrovirens
10年后的今天,新喀里多尼亚原来的单一物种已经分出了3个物种。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但彼此之间甚至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而且这个蓝蘑菇至今还没有被命名。
我觉得这种蘑菇太迷人了。Tom May博士把它叫做“澳大利亚最美的蘑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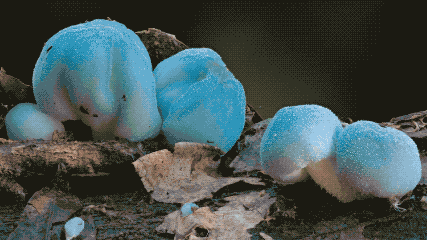
我一直在尝试,想为它拍一个延时镜头,有时候真的拍成了。

像这样的科学合作,是真菌改变我看世界的下一个重要阶段。
2014年我收到Peter Mortimer博士的邮件,他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教授。Peter和系主任许建初教授带领了一队真菌学家。他们在做的真菌研究非常激动人心。Peter的父亲在南非,他看见我在网上发的照片之后,提议Peter联系我。第一次通邮件的成果最终促成了四次云南之旅,拍摄并记录了偏远的亚热带森林中的真菌。
正是在这一次次实地考察中,我意识到可食用的真菌种类是多么丰富。
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是所谓的“真菌恐惧症”社会。在我们的超市里只卖大约五种蘑菇,而且它们看上去相当无聊。人们普遍不太敢吃森林里的菌类,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些蘑菇有毒,哪些蘑菇可食用。
但是在云南,我们发现人们食用的菌类多达900余种。绝对是一个“视菇如命”的社会了。
我必须坦白地说,在家的时候我不太爱吃蘑菇。但在云南,人们把美味的蘑菇介绍给我们,当地村民还分享了哪些蘑菇能吃,以及如何烹饪的知识。我们还发现在中国,蘑菇可是一门大生意。
在中国的森林里,我们开始了解树木、动物和真菌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于是我对世界的看法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森林于是开始有了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一大堆树而已。即便是林下结构相对简单的森林,可能也有成千上万种生物。所有生物都相互依存,所有生物都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森林”。从病毒到细菌,再到真菌、植物和动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而复杂的生命网络中的一份子。而真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确实非常地重要,但我们对它们仍所知甚少。
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中,我们记录的物种有七分之一是新发现的物种。就算是那些已知的物种也足够让人着迷了。
这里有几种我觉得特别令人激动的。
这种蘑菇叫鸡枞。我在云南第一次拍了它们。

它们有相当坚硬的菌盖,使它们能够从地表以下一米的地方穿透地面。

它们还和白蚁互惠共生。这表示这两个物种都无法离开对方而生存。白蚁搜集草木,然后把它们带回地下的蚁穴,在那里为真菌提供养料,之后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真菌。这些菌类最终会结出子实体,把它们的蘑菇推到地面以上。
鸡枞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好多好多白蚁,却没有鸡枞。
这种真菌的许多个种,在整个亚洲热带地区和非洲都能找到。这种真菌的其中一个种,产出的蘑菇最多有1米宽。
许多鸡枞都被视作美味的食用菌类。我们经常在这一地区的市场中看见它们。我们当然很喜欢它们了。
这种小小的紫蘑菇叫做紫蜡蘑,和松树是共生关系。

▲ 紫蜡蘑
云南的村民特别稀罕这种挺值得吃的蘑菇,因为它放在什么菜里都好看。我就喜欢它这么漂亮的颜色。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蘑菇当属鹅膏菌属,伞形毒蕈,俗称死亡帽。它们生长在橡树下。每年世界上都有人因为吃这种蘑菇丧命。例如我们在缅甸记录的这种鹅膏菌,

▲ 鹅膏菌属,缅甸
我们认为它就是伞形毒蕈属。它可能是一定数量的食用蘑菇致死案例的罪魁祸首。与我们合作的真菌学家,还有当地的村干部都很想记录下这种蘑菇,好提醒人们不要食用它。
但这种鹅膏菌和尼泊尔人说的可食用菌类是很相似的。

它们之间看上去没有多大差别,不是吗?据说这种蘑菇味道相当不错,但我恐怕真的是验证不了了。
你们知道吃了这种伞形毒蕈之后会发生什么吗?首先出现的症状是:你会在第二天感到有点恶心,三四天之后你太难受了,知道自己必须去看医生了,可到那时候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伞形毒蕈内含可以毁掉我们肝脏的毒素,慢慢地,我们会在几周之内死掉。
这种蘑菇我们必须得避开。所以毫无疑问,摄影对于教育大众,对于告诉他们这些蘑菇的信息,还有哪些是毒蘑菇起到的作用都非常重要。正如教育人们去了解哪些蘑菇可以吃一样。
和中国合作之后,我们又和尼泊尔、缅甸、印度开展了类似的合作。我们和专注于保护的组织合作,帮助当地人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森林。

往往随着道路的修建,森林被砍伐,这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利的。森林中的可使用菌类原本可以食用或交易,最终也随着森林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这些照片可以为这些国家的村民提供实地的指南。
但对我来说最最激动的,是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带记录那里所有的真菌,并了解到每种真菌如何与森林互动的一个侧面。
喜马拉雅东部的真菌绝对是精美绝伦。

▲ 喜马拉雅东部的真菌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作为真菌教育者的角色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在这场踏遍国际的真菌冒险中,我们经常向我们的合作者们介绍第一次接触到的真菌。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对他们从未注意过的世界兴奋不已。每一次,我们都发现他们几乎和我们一样热情满满、沉迷其中。
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在国际范围内推动这件事。所以在2018年,我们在印度拍摄了整个真菌“游猎”之旅。下面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点心得体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记录的梅加拉亚邦(印度东北部)的发光蘑菇。
01:46
目前地球上大约有80种有记载的发光真菌。但其中只有少数真菌比这种亮。这是莫里农地区第一次记录发光真菌。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现在我带你们回到我在澳大利亚的家吧。
2019年,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之一。17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光是我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就有500多万公顷被吞没在大火中。山火的破坏力非常骇人。尤其是当它开始烧毁我们住处附近的雨林时,更让人害怕。

大火过后的几天,我们听到消防员说灰烬中出现了蘑菇。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了那片焦黑的地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些什么。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那里到处都是蘑菇。还有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品种。
这种蘑菇叫Stonemaker Fungus。

它会在地面还在发热冒烟的时候开始出现。它常年长在土里,在地下形成了坚硬的菌丝块,形似石头。故得名。

它只有在有火的时候才能长出子实体。而在这片森林中,这种事可能一百年才会发生一次。
然后我们看到大量的小小的盘菌覆盖在地表,我们成功辨认出它们就是Anthrocobia mueleri。

我们开始好奇它对森林土壤的保护作用。因为大火会让土壤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被水冲走,或者被风吹走。但这种真菌似乎可以将表层土壤捆在一起,锁住了水分。
对我而言,这些真菌提出了太多太多的问题。比如:在没有火的情况下,这些真菌在哪里生长呢?我看不出它有任何深层的菌丝留存。
我在书中读到过,在北美有一种类似的菌类,作为一种微型真菌生长在苔藓的细胞结构中。

也许这种Anthrocobia mueleri也是类似的物种。只有当火将土壤中所有竞争养分的生物体进行杀菌之后,它才会长成大型真菌。
我们甚至在森林的地面上,在曾经有原木倒下的地方,发现了木炭下的蘑菇。这里应该是火势最猛烈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呢?孢子又是怎么进入到这片已经被大火彻底消过毒的土壤呢?
爱火的真菌种类之多,让人叹为观止。

在我们回去了一个月之后,又有不同种类的真菌涌现了出来。

我们发布了几个视频,反响让我们感到惊喜。许多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所有毁灭性的新闻中,这些积极的信息振奋了他们。他们欣喜地听到森林的复原力有多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归功于森林中的真菌。
生命是如此美好,而我们对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所知甚少。就像我在一开始告诉你们的那样,我曾经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从事庞大的计算机系统工作。我们认为这个系统非常之复杂。但计算机系统是由人类设计出来的,所以只要聚集足够多的人,我们就能解释关于它的一切。
可就算是自然界中最微小的生物体,也要比庞大的计算机系统更复杂。而当你意识到我们的星球有万亿,甚至千万亿个这样的生物体时,我们就对地球上生命的复杂性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开始了这段旅程,对摄影略知一二,却对自然界所知甚少;认识到真菌的复杂性,并通过它了解到生命的复杂性。我现在明白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之间的联系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
我们仅仅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生物体,但我们却掌握着足以摧毁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手段和权力。毕竟我们无法独自求生。我们创造了这么多非同一般的工具,人类也因此拥有了去了解和保护的契机。
我想我被赋予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帮助记录下这一复杂体中微小的片段,然后和你们分享。
从地面上那个小小的紫蘑菇的照片开始,我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揭示地球上生命全貌的旅程。



编辑:陈显琳
核校:郭小花
来源:一席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