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父变星”的故事,点亮烛光,照亮宇宙的女天文学家
想法捕手2020-03-17 12:49
1920年4月26日,在纽约史密斯森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天文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世纪大辩论。
辩题是“银河系是不是宇宙的全部”。
这场辩论中的两大主辩,一个是主张“银河系就是全宇宙”的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pley),一个是主张“银河系只是宇宙一小部分”的希伯·道斯特·柯蒂斯(Heber Doust Curtis)。
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涡状星云到底为何物,是遥远的另一个星系?还是飘荡在银河系里的气体云?
双方唇枪舌战,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论与数据层出不穷,如同天文学的世纪大汇报。
然而,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为没人能回答涡状星云与我们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仙女座里的变星
仙女座里的变星直到1924年,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的哈勃在仙女座大星云M31中找到了一颗明亮的“造父变星”,才测出M31至少距离我们上百万光年,第一次证明了河外星系的存在,终结了4年前的那场世纪辩论。
为什么找到“造父变星”就能测出星系与我们的距离?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终生与病魔抗争的失聪者;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沉默寡言的悲情人物;一个拿着微薄工资却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养活了成千上万名博士生的本科生;一位名叫亨丽爱塔·勒维特(Henrietta Swan Leavitt)的女天文学家。
 亨丽爱塔·勒维特
亨丽爱塔·勒维特一次不幸的毕业旅行,一生的失聪与病痛。
1892年,勒维特毕业于七姐妹学院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
而在她满心欢喜的毕业旅行中,24岁的勒维特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变故。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损伤了她的视力与听力,也摧毁了她活泼开朗的少女性格。
病后她的视力虽然得到了好转,但听力却每况愈下,最终失聪。
面对变故,成长于牧师家庭的勒维特,只得寻求信仰的庇护,将疾病带来的苦痛慢慢沉淀,然后毅然决定继续攻读天文学硕士学位。
第二年,便跟随她的导师爱德华·查尔斯·皮克林(Edward Charles Pickering)来到了哈佛大学天文台(1877年-1919年)工作与学习,成为了一名“计算员”。
 哈佛天文台,摄于1899年
哈佛天文台,摄于1899年所谓的计算员,实际就是充当人肉计算机的作用,每天处理大量枯燥乏味的数据,运算、检验、核实。
但顽疾缠身的勒维特时常生病,不得不频繁请假,这让她的科研工作一团乱麻。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将无法完成学业,1896年勒维特选择了放弃,主动离开了哈佛大学天文台,一走6年。
在这6年里,即便她拥有不错的学历、聪明的头脑,但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勒维特举步维艰,更充分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失聪者的生存压力。
1902年,她不得不写信给皮克林,希望能再次回到哈佛大学天文台,只为获得一份能维持生计的工作:每小时30美分的工资(男性工资的一半)。
这个沉默、冷静、专注的学生,曾给皮克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于是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她糟糕的身体状况,让皮克林十分担心她会影响团队的工作进度,所以并没有让她参与当时恒星分类这样的团队工作,而是让她独自一人去研究“变星”(variable star)这个冷门领域。
所谓变星,其实是恒星中的异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光亮的变化。造父变星、新星、超新星都属于变星。
在20世纪初,变星问题属于当时无人敢踏足的科学荒原,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只有一堆繁杂的数据,以及印满斑点的玻璃底片。
在变星中最为特殊的就是“造父变星”(Cepheid)。
之所以称为“造父”其实是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命名。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是很发达的,就新星的识别和命名来说,长期领跑全球。所以“造父”这个名字早已有之。
给发现的新星命名是一个艺术活,而艺术源于生活。
造父是西周时有名的车夫,是如今的赵姓先祖。
此人善御,据《史记》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可见此人既能上天见得了西王母,又对君王有功,当然就能留名了。
而英籍荷兰天文学家约翰·古德利克(John Goodricke)第一次发现的有光变周期的恒星正是这颗造父一,也是西方的仙王座δ(Cepheus)。此后这类变星就都被称为造父变星,英文名:Cephe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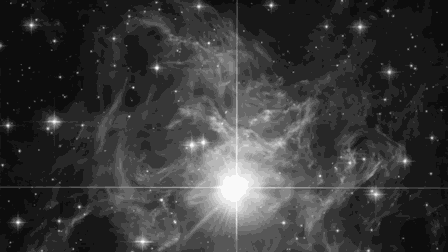 船尾座RS是银河系中最亮的造父变星之一
船尾座RS是银河系中最亮的造父变星之一这类恒星无论光变周期长短,总是先亮后暗,然后再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类恒星大都走到了生命尽头,核心处氢消耗殆尽,开始聚变其他元素,内部压力变得不稳定,由此导致了恒星大气层就像火山一样有了积蓄、膨胀、爆发、冷却的周期变化。
静默无声的开挂技能,找变星的高手。
要研究这些造父变星,第一步当然是要先识别它,而识别它的关键就是发现其是否具有周期性光亮变化,而要发现变化,就必须反复在大量观测数据中找寻、对比、核实。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仅靠人力,这确实是一件极其考验耐心与专注的工作。
不过可能由于失聪,勒维特的专注力变得更为惊人,可以一连七八个小时的投入到拿着放大镜找星星的游戏中。
仅过了一年多时间,勒维特把这份数星星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堪比找茬的“最强大脑”。
从1904年开始,勒维特以惊人的速度在麦哲伦云中不断发现新的造父变星。
她找得实在太快,以至于有天文学家专门致信皮克林:“勒维特小姐是寻找变星的高手。我们甚至来不及记录她的新发现。”
1908年,勒维特将自己在麦哲伦云中找到的总共1777颗造父变星进行了整理,并作为论文发表在了《哈佛天文台年鉴》上。

而在这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人们找到的造父变星不过才区区几十颗。也就是说,她一人完成了百年时间内所有天文学家上百倍不止的变星识别工作。
这惊人的数量对比,引起了天文学界的轰动。
但勒维特论文中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她发现的变星数量,而是最后对其的总结。
勒维特挑选了16颗位于小麦哲伦云中的造父变星,并为它们列出了一个光变周期与亮度的对比关系表,随手留下了一条评论:“这值得关注,变星越亮则其光变周期就越长。”
照亮宇宙的“标准烛光”。
从1908年开始,勒维特开始特别关注造父变星,并完善她的发现。
然而不久后,她再一次病倒,直到1911年秋才回到哈佛。
第二年,勒维特将之前在小麦哲伦云中挑选的16颗造父变星增加到了25颗,并把它们画在了一张以周期(对数)为X轴,以亮度为Y轴的图上。勒维特惊讶地发现它们排列成为了标准的直线,由此断定“造父变星的亮度与其光变周期成正比”。
 两条直线上分别是变星的最大和最小亮度
两条直线上分别是变星的最大和最小亮度这就是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也被称为“勒维特定律”。
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不亚于哈勃定律:“星系距离我们越远,退行速度越快,且退行速度与距离成正比。”
勒维特为天文学发现了一把“量天尺”,让天文学家能够运用“标准烛光”来测量遥远的星系。
标准烛光测距的基本原理,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简单常识。同样一根蜡烛,从不同的距离上来看总是近亮远暗,而且亮度减弱与距离成平方反比关系。
因为宇宙是一个三维立体空间,任何一点的光源都是以球面向四面八方传播,因此一个稳定光源射出的光子数,必定随着距离的增加,以平面反比的关系消减。也就是说距离增加一倍,亮度减少为原来的1/4。这和引力的衰退方式一样,其本质是宇宙的大空间结构。

在勒维特发现造父变星的秘密之前,我们很难确定一颗耀眼的星星到底是因为离我们近而耀眼,还是其本身比其他星星更亮。
所以说,勒维特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因为勒维特挑选的造父变星全都位于小麦哲伦云内,因此可近似认为它们与地球的距离都相等。那么只要可见亮度相等,它们的实际亮度就一定相等。
而造父变星的实际亮度与其光变周期成正比。这意味着,只要光变周期完全相同,它们的实际亮度就完全相同。
就这样,造父变星成为了天文学历史上发现的第一种标准烛光。(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更为精准的la型超新星作为标准烛光)
在勒维特的造父变星周光关系公布一年后,埃希纳·赫茨普龙(Ejnar Hertzsprung)第一个用视差法确定了“造父一”的距离——890光年,相当于为勒维特发现的“量天尺”刻上了第一个刻度。
1921年,当世纪大辩论中的沙普利继任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时,勒维特才被提拔为恒星光谱部门的负责人,而至此她依然是一个本科学历,拿着每小时30美分的“计算员”。
也就在这一年,勒维特再次病倒了,这次是致命的癌症。
在双12的一个雨夜中,勒维特离世,留给了她母亲只够买8条地毯,价值315美元的遗产。
去世后,勒维特被葬进了家族墓地之中,没有自己单独的墓碑。她的名字与十几个亲戚的名字挤在一起。
 勒维特之墓
勒维特之墓就这样,勒维特结束了作为“计算员”的一生,生前从未得到天文学家的待遇。
因为在那个时代,她仅仅是用笔和纸进行大量冗长计算工作的“计算员”,并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拿着放大镜在玻璃底片上找星星,而不是透过望远镜。
直到1925年,一位瑞典科学院的院士写信给哈佛大学天文台,打算提名勒维特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才从沙普利嘴中得知勒维特已经去世4年了,而诺贝尔奖永远不会颁给去世的人。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