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夏天,为什么离不开芝麻酱?
每日人物社2019-06-23 22:31

庞各庄的西瓜红了瓤,小铺里冰镇上北冰洋,老家儿煮好了绿豆汤,过水面配上芝麻酱——一个经典的北京夏天不过如此。
特别是那一碗芝麻酱凉面。有人说,一到夏天,北京人厨房里一半的芝麻酱就都用来拌面了。煮好的手擀面过了凉水,黄瓜细细切成丝,醋和蒜汁一起浇上,添一勺澥好的调味芝麻酱,热气蒸腾的酷暑里,没有什么比这一碗面更顺口的了。
而北京人对芝麻酱的爱又岂止是在夏天,曾经有人总结:北京人的命,就是芝麻酱给的,流淌在北京人身上的血,也都是芝麻酱口儿的。
文 | 韩逸
编辑 | 金石
插画 | 陈聃
设计 | 震震
“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芝麻酱”——这话是老舍先生说的,出处是汪曾祺先生写的《老舍先生》——有一年,北京城的芝麻酱缺货,老舍提案要求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因为,“北京人的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粮油副食店就恢复了芝麻酱供应,汪曾祺佩服老舍,“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
电视剧《求佛》里,陈宝国饰演的胡同串子侯三吃芝麻酱凉面的形象就是北京人过夏的标配,一手端面扶筷,一手抓根黄瓜,一口咬下去,嘎嘣脆,喷喷香。
有人说,一到夏天,北京人厨房里一半的芝麻酱就都用来拌面了。煮好的手擀面过了凉水,黄瓜细细切成丝,醋和蒜汁一起浇上,添一勺澥好的调味芝麻酱,热气蒸腾的酷暑里,没有什么比这一碗面更顺口的了。做麻酱凉面出名的新川面馆,会额外在面里加点芥末,提气又刺激,天热的时候,想排个位子都难。
还有年轻人在老配方的基础上搞了点创新——雪碧麻酱凉面成了北京年轻人的新宠。雪碧、麻酱、蚝油和老干妈,混出了看似奇怪但口感非常惊艳的口感,麻酱的香加上雪碧的爽甜,被评价为“真的没胡闹!味道有点妙!”
其实,不止是夏天,北京人恨不得一年四季都跟麻酱腻味在一起。京味儿特色小吃几乎都躲不过芝麻酱的搭配。爆肚开水一焯,全靠芝麻酱提味儿。凉拌茄泥、凉拌豇豆、凉拌白菜、凉拌西葫芦……都浇着芝麻酱,吃面放芝麻酱,花卷烧饼里都是芝麻酱。就连冰棍、威化和面包,都难逃芝麻酱入侵——难怪曾经有人总结:北京人的命,就是芝麻酱给的,流淌在北京人身上的血,也都是芝麻酱口儿的。
全国各地的特色菜,进了京也得过麻酱这一关。陕北的米皮面皮没能挺住,四川的麻辣烫也不曾幸免,就连香油蒜泥的经典火锅蘸料,也被老北京人二话不说,招呼上一勺子麻酱汁,麻酱纳百川,调料大团结。
北京人为什么如此爱芝麻酱?这一口芝麻酱又蕴藏着多少北京人对于生活的仪式感?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半年,我们完成了一次极具“酱心”的“芝麻酱深度游”,关于芝麻酱的一切,你或许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第一站 赵府街副食店

鼓楼大街后身儿,有一条张旺胡同,从前住过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如今“住”着一个网红商店——全北京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赵府街副食店。
从成立的那天起,赵府街副食店的一天,永远都是从打芝麻酱开始的。早晨7点开门之后,买酱的人就很少间断。“我们北京人啊,就离不开这个。”拖着拖车带着酱罐子来打芝麻酱的北京人,使劲吸着鼻子,好像想把回忆里的香味儿一起吸进肚子里带走。
老板李瑞生今年刚满60岁,已经在这里打了32年的芝麻酱,早练就了一勺准的手艺。缸沿上横一柄长勺,说好打多少,手腕子一抖,绸缎子一样的芝麻酱变成细细一道,流下来,到了量,再一收,芝麻酱就乖乖回到勺子里,不论多粗的瓶口,酱绝不洒一滴到瓶外,“一勺准”。

芝麻酱从勺子里细细一道,流进罐中。图/ 韩逸
这手本事跟当年的物资匮乏有关。那个年代,芝麻酱和糖油酱醋一样是稀罕物,要拿着副食本购买,没法敞开了吃。1956年到1992年之间,赵府街副食店每月定量售卖400斤芝麻酱,供应着周边1300户人家,每人每月一两,都是定数。“你给上家多打一点儿,就要有一家少打,所以一点也不能差。”
90年代以前出生的北京孩子也就因此有了一份艰巨的任务——打麻酱。
打酱不难,可是怎么把一罐芝麻酱完完整整地带回家,就成了一项艰巨的挑战。那个吃肉难的年代,大伙儿嘴里都没有味道,藏在柜子顶上的醋都有人偷喝,副食部门口垛着的大白菜都有孩子偷吃,别说香喷喷的芝麻酱了。小孩子没法抵抗这种诱惑,把手伸进碗口,顺着碗沿儿这么一抹,直接送进嘴里。砸吧砸吧,芝麻酱的香味儿马上漫进整个口腔。
这几乎是一代北京孩子的共同记忆——一路走,一路吃,从副食店出门时芝麻酱还有一斤,到家时还有多少就难说了。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大人派孩子去副食店打芝麻酱,回来发现分量不够,于是找到副食店去理论,要求重新称,售货员说,您最好先称称孩子。
蘸——也成了芝麻酱最基础的吃法之一。豆泡汤要蘸芝麻酱,爆肚也要蘸芝麻酱,铜锅涮肉更要蘸芝麻酱,但最经典的吃法还是蘸馒头——伸手掰了热馒头,蘸着芝麻酱夹白糖。芝麻的香气从馒头里透出来,真能直接唤起人对食物最原始的感情,香,甜,生命的大满足都在这一口馒头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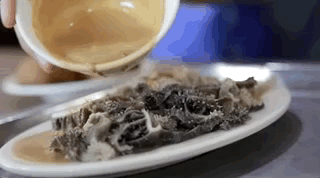
爆肚淋上麻酱。图/ 韩逸
当年的稀缺使得芝麻酱成了北京人最深刻的味觉记忆,如今,日子好了,很少有人再用热馒头蘸芝麻酱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芝麻酱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它早已成了融入北京人生命中的味道,无处不在。
如今,赵府街副食店里那9个装酱的百斤大桶仍然齐齐地列在长条木柜台周围,900斤酱还是经常不到一周就被卖光。
“别小看这两口缸,一般人不见得看得住。”李瑞生说,看缸有讲究,夏天如果落一只苍蝇,那就要坏一缸酱。他原本今年3月退休,但怕旁人再也找不到这口老味道了,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卖酱。

在店里忙活着卖芝麻酱的李瑞生。图/ 韩逸
“甜口,出数儿。”这是李瑞生总结的自家酱的优点。如今,超市里卖的芝麻酱分两种,一是纯芝麻酱,还有一种混合酱。芝麻味苦,混上口感偏甜的花生酱,既能保证香气,又能改善口感。老北京人小时候吃的“二八酱”,就是芝麻酱和花生酱以2:8的比例混合成的混合酱。
“别地都没有这个味儿了。”打酱的客人来自北京各地,他们都觉得,李瑞生这里的芝麻酱还是小时候吃的那口的味道。这份儿讲究,让李瑞生成了小小的网红。赵府街副食店也成了鼓楼胡同里拉车师傅经过时都会停下来的一个景点,游客进来拍完照,少不了带两罐酱回家尝尝。
外地人不太了解芝麻酱的具体吃法,常常会问“芝麻酱怎么吃啊?”这时,甭管是来店里打酱的老北京,还是李瑞生,都是一句话:“芝麻酱能怎么吃啊?蘸~~~着吃啊!”

陈晓卿曾在《圆桌派》里表示,在北京芝麻酱配什么都可以吃,能蘸全宇宙。图/ 网络

第二站 顺义燕桥牌香油厂

为了保住那口芝麻酱的味道,李瑞生换了好多家供货商,好酱孬酱,尝遍了北京周边的芝麻酱厂之后,李瑞生认定了一家香油厂的二八酱。
顺着李瑞生家香油瓶子上印着的地址,不难找到顺义的燕桥香油厂。香油厂设在远郊,距离赵府街40公里,进了厂房门,香味儿直冲鼻子。
香油厂成立于1989年,副厂长李怡东从食品工程专业毕业之后,来到香油厂做销售,跑遍了全北京的大小超市。
对于老北京人最认可的二八酱,李怡东说了一个秘密,他厂里酱的比例早不是严格的“二八”了。后来,李怡东觉得八分花生太甜,为了增加芝麻的香气,试着提高了一点芝麻的比例,“现在呀,其实更接近三七”。
比配比更重要的是原料。芝麻从产地就能分出高下。李怡东尝试过很多地方的廉价芝麻:苏丹的,缅甸的,莫桑比克的,坦桑尼亚的,“都不行”。香气少,发苦。只有埃塞俄比亚的一级芝麻还行,味道最接近国产芝麻,可是磨出酱来,口感还是稍微差一点。最终,他们坚持用湖北孝感和安徽阜阳两个地方的芝麻。

来自湖北和安徽的芝麻,被倒进工厂的机器石磨,即将完成从芝麻到麻酱的华丽蜕变。图/ 韩逸
磨酱的工具也有讲究。香油厂里至今有两台工作了十几年的青石磨,是用石景山模式口的青石打磨的,那里旧时叫做“磨石口”,专产给宫里御用的石料。这种石头磨出来的芝麻酱,细腻得像牛奶巧克力一样丝滑。

丝滑的麻酱从工厂石磨下流出。图/ 韩逸
可真要磨出来一碗好酱,原料和工具都不是最重要的。李怡东说,“靠得还是良心。”走南闯北进货的时候,他见过更多行业里掺假作妖的花样儿。掺黄豆的算是良心,掺方便面渣的大有人在。还有人到天津的麻花厂去收购过期的麻花渣,动辄几百几千斤,碾碎,往芝麻酱里一掺,比纯芝麻酱还好吃,“有股特殊的香味儿。”
在香油厂一干这些年,李怡东赶上过芝麻酱的黄金时代。“最有名的那几家馒头品牌,用的都是我们家的麻酱。”那是上世纪90年代,生意好的时候,每三个月左右,60吨来自湖北和安徽的芝麻就得坐着火车进京,香油厂的石磨转到滚烫,即便吹着工业电扇降温,也得每工作一小时就休息冷却一小时。
后来,生活越来越好了,李怡东明显感觉人们对芝麻酱的热情淡了。北京周边的芝麻酱厂也在渐渐减少。如今,燕桥香油厂已经是北京城郊为数不多生产芝麻酱的厂家了,其他的要么关门,要么搬到了河北天津。李怡东挺理解人们喜欢尝鲜的心,可他也挺怀念过去芝麻酱蘸一切的日子。“过去穷,人都想法设法地把一个东西吃出花样,就是一个馒头,也活出滋味来!”
但这口芝麻酱,是流在北京人血液里的,不是那么容易撇下。这几年,“那股风过去了,”李怡东发现,老北京的铜锅涮肉越来越流行,老客人又打了电话来,张口就定原早的芝麻酱。成箱的芝麻酱又开始往外发,如今一个月就能用上30吨芝麻,是90年代消耗量的1.5倍。
美食公号“三匠厨房”曾经分析过,北京人对芝麻酱的爱,或许根植于一种“匮乏的博大”,“即使曾经贫穷、捉襟见肘,人们也努力在有限的食材中发展出一种精致、一种讲究,尽管日后芝麻酱白糖蘸馒头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是饮食记忆和文化却留存了下来,影响着一代代的北京胃。”

撒上芝麻的麻酱烧饼,是北京人经典的早餐之一。图/ 韩逸

第三站 前门张记涮肉

除了打了芝麻酱就偷吃的孩子,绝大多数人吃芝麻酱的第一步都是——澥。
芝麻有油性,吸水,用水去和芝麻酱,只要沿着一个方向不停搅拌,酱会变得比原先还要浓稠。得再加水,不停地搅,才能逐渐适口。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芝麻酱吃着糊嘴,那是没有澥好,水加少了的缘故。
57岁的张学铭,当年也是回家路上偷吃芝麻酱的馋孩子,如今,他料理着位于前门的张记涮肉,算是北京人中最后一拨会用老规矩澥芝麻酱的人之一。
他的店在许多北京涮肉推荐里榜上有名,在很多美食家心目中,其他火锅不分先后,张记涮肉单列第一。王家卫导演曾经在他那儿吃过一回涮肉,临走给他一句话,“您这个店,是米其林的标准。”
像很多注重食材的米其林星级餐厅一样,张学铭固守着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对于那碗老北京涮肉蘸料的配置,他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最基础的芝麻酱要好酱。送来的酱,他会用一根长长的擀面杖一捣到底,上下必须一个味儿,掺不得假。
配料更是样样讲究。青头的小小的海白虾,先发酵,再高温爆炒,把虾的腥味儿爆出去,只剩下虾香。其他弃了不要,虾油入芝麻酱来调。当季的韭菜花摘回来,冲洗干净,阴干20来天,到没有多余的水分,才能腌制。

将虾油、酱油澥进芝麻酱。图/ 韩逸
酱里的果香来自当年下来的京白梨。先焖制一个星期,要提防不能焖坏。等到白皮变黑,拿刀一拍。梨肉已经变沙,再焖个透,然后一层一层撒到缸里,加上其他辅料,最后顶上撒一层桂花,封盖。
澥芝麻酱的料水也不是普通的白水。水里加了香叶、肉豆蔻,小茴香等等香料泡了,再高级一点,用柴鸡煮了高汤,纱布沥干,没有一点杂质,鸡油也沥掉了不要,用鸡汤和料水来澥芝麻酱。
澥的过程也讲次序。先放料酒、虾油、酱油、韭菜花,搅匀之后,再放酱豆腐和芝麻酱,先下液体,再下固体,酱料不粘碗儿。要慢,水要一点点加,心急容易澥得清汤寡水。用料汁澥则要均匀粘稠,厚了拌不开,容易搅打在筷子上。
对于澥芝麻酱,还有认真的美食家专门写文章论证过用水还是用油,“有的人用香油代替水澥芝麻酱,我以为并不可取,因为芝麻酱里本来就含有大量油脂,以油澥酱,太过油腻。”
老张自有办法。夏天,加上一点山楂汁,山楂的酸味可以中和油腻,“客人会多点几盘肉。”这样做出来的酱料,叫做七彩香。一碗七彩香,像极了《红楼梦》里叫刘姥姥咋舌的茄鲞,一个再普通不过茄子,“我的佛祖,倒得是十来只鸡来配它!”
张学铭坚持这碗酱是不能用羊肉直接去蘸着吃——刚涮好的羊肉带水,会稀释酱料,越吃到后来味儿就越不对。所以,要把酱料往涮好的肉片上泼。这一口下去,羊肉的鲜甜,麻酱的香气,海白虾的鲜味儿,豆香,酱豆腐的咸香,最后是京白梨的果香,随着羊肉温度的变化,在嘴里慢慢感受味道的不同层次。

老张说,往肉上倒酱汁才能保证口感的层次,不让涮肉上的水稀释芝麻酱的味道。图/ 韩逸
尽管如此讲究,但张学铭依然有点失落,因为小时候闻见隔壁吃麻酱面和麻酱蘸馒头的那个幸福感,已经很难再出现了,“从前,我们哪家吃个麻酱面,您别告诉您吃面,一切黄瓜丝儿,那黄瓜的清香就飘过来了。”

码上黄瓜丝的麻酱面。图/ 韩逸

第四站 百年义利巧克力分厂

麻酱威化是“芝麻酱周边”中的一个传说,全名叫“麻酱威化巧克力”,代号是6952,这是百年义利特有的编码方式,表示是1969年的第52号产品。威化的馅儿都是芝麻酱,挂了巧克力酱就是威化巧克力,不挂酱就是麻酱威化饼干。
是谁最先提出来往威化饼干里加芝麻酱这事儿,韩俊已经考证不到了。他从在百年义利学徒开始,这个甜品就是90年代的明星产品。当年人们排队疯抢麻酱威化的架势,绝不弱于今天的小年轻等待喜茶。不一样的是,喜茶耐心点总能买到,麻酱威化却不是轻易能等来的。
“供不应求”。夏天最热的月份一过,韩俊就要跟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备货。一个人看六个炉子,8小时,压制1100张威化皮子,然后一层皮子一层酱,四张三层,一压,一切,就是成袋的麻酱威化了。
260多个工人,分成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一天能出2吨威化巧克力。可就是这么加班加点,是到了八月十五,麻酱威化仍然是一上货架就卖空的爆品。

百年义利著名的麻酱威化。图/ 网络
临近过年,韩俊总能看到有中年人蹲在机器后面嗷嗷痛哭——那准是安徽或者河北的供货商,每天住着旅馆,消耗着车马,排队来等着进麻酱威化的货,可是等不到。
大型超市里的销售奇迹也是那时候的麻酱威化造就的。角楼旁边的万客隆,就被盒装908g的麻酱威化巧克力创下了单品销售的记录。在九十年代末,一盒不到30元售价的麻酱威化,一个月内创造了70万的销售额。产品火爆之后,雀巢和稻香村坐不住了,也开始陆续推出麻酱威化巧克力。
“整个义利销售额一个多亿,我们威化巧克力占2000多万。”如今,回忆起自己当年手工生产的麻酱威化的时候,已经退休的韩俊身子斜在椅子里,仰着脸,眯着眼,一说一顿,好像还在咂摸生产线旁边儿的麻酱香味:“非常好吃,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麻酱威化。图/ 韩逸
在当年,麻酱威化好吃到就连边角料也不会被放过。那时候麻酱威化的名字叫做“味得酥”,切剩下的边边角角,叫“味得酥边儿”,也会单独包装售卖,销路比威化还好。一是便宜,二是压制威化的过程中,芝麻酱馅被挤到两边,会溢出一些,反倒因为芝麻酱多,更香。
北京百姓把麻酱威化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十几块钱的一大袋子,普通人家可以吃很久。小孩子把大块的挑出来吃了,大人再把剩下的渣渣沫沫抹出来,这里面有酥脆的膨化皮子,有麻酱,有巧克力,磨碎了一冲,喝得一点儿也不剩下。“太棒了,那可比油炒面好吃。”
如今,麻酱威化早已没了当年的火爆,但它仍是芝麻酱渗透入北京人生活的每个缝隙的例证,一位外地人如此记录他在百年义利的门店里看到麻酱威化后的心情:“北京人真是将吃麻酱发挥到了极致。”
一个彩蛋 一个被芝麻酱支配的重庆人
重庆人刘璐在北京开了三年火锅店了。他对“不放麻酱”的坚持也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刘璐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他尽了全力来保证自己店里的正宗重庆味道:毛肚、黄喉、鸭肠、鹅肠都是从重庆空运过来,锅底是牛油红汤,冰粉儿里的红糖都是云南古法制造,蘸料只有蒜泥香油和干蘸料。
连葱花香菜都没有。他记得小时候的重庆老火锅,根本没有葱花香菜,每桌上一个小盆,蒜泥满满的,自己舀。他甚至连味精都不乐意放,只在桌上搁一个小盐罐子,客人可以自己调整咸淡。
可是客人不答应。
不论是北京人,还是在北京住着的外地人,都会主动问有没有麻酱蘸料,好像这东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存在。还有人因为店里的小料不是自助小料,进了门又掉头出去。
刘璐没觉得怎样。一开始,他觉得这是客人的选择。直到有一回,他去吃了心目中很正宗的杨家火锅,那的自助小料也配着麻酱。刘璐妥协了。“你是商人嘛,这是商业。”两年前,他在三里屯SOHO开了新店,有了麻酱。
如今,刘璐的店里,麻酱成了卖得第二好的蘸料。作为重庆人,他唯一坚守的底线是——自己家里从来没存过这种调料,店里的料都是师傅调,他从来不问。
来北京16年,他只有一次觉得麻酱也还挺好吃的。新店装修的时候,刘璐天天蹲店。有次忙过了饭点儿,在门口将就了一顿麻辣烫。看着满满一勺麻酱浇上,他有点无奈,但吃进嘴里,味道竟然意外得挺好。“也可能就是太饿了。”刘璐想了想,那是唯一一次和麻酱版麻辣烫的亲密接触,自那以后,这位重庆人再没主动去吃过。
加 映:一碗芝麻酱凉面的诞生
酷暑难当,记者同志亲自下厨,给大家上一碗(假装)正宗的芝麻酱凉面——

关键在酱。两勺芝麻酱,加上清水五勺开搅。朝着一个方向转动,芝麻酱因为吸水而逐渐变稠,搅到搅不动了,放盐,鸡精,味极鲜继续搅动到稀厚合适。黄瓜切丝,其他面码比如豆芽香椿焯熟切碎。面煮8分熟,捞出来在水中冲凉,装盘。加澥好的酱汁,面码装盘,撒上白芝麻,辣椒油,拌好,开动!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