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开头,王战团正在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
滑稽之余也令人深思。这是电影《刺猬》名字的来由。
电影由顾长卫导演、改编自短篇小说《仙症》,小说作者郑执,与班宇、双雪涛被坊间统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拥有这种创作基因的《刺猬》,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一家人。
葛优扮演的王战团是个“精神失常者”,王俊凯则扮演他的小侄子周正,一个轻微自闭的少年。生活在一个强调集体的年代、一个重视家族概念的地域,两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令他们被逼退至社会边缘。
尽管讲述边缘,《刺猬》并不伤痛。它的话语基调是平静的,有时甚至轻快、生动,颇有趣味。它描写了王战团与周正横跨十几年的隐秘羁绊:起初,年幼的周正是唯一可以理解王战团的人,后来,周正被家庭与学校围剿,王战团是他唯一的精神依赖。

《刺猬》海报
在家人们眼中,王战团和周正是异类。他们都“疯了”。
而《刺猬》让人看见,“疯了”的另有其人。
(本文轻微剧透)
是谁疯了?
影片中,王战团有两句基准台词。一句是:“叫我王战团。”无论对侄子、女婿或者任何人,他都这么介绍自己。

王战团(葛优 饰)
原著小说中,年幼的周正担心“直呼长辈姓名不礼貌”,王战团说:“礼貌是给俗人讲的,跟我免了。”
他又追了一句:王战团就是王战团,我娶了你大姑,不妨碍我还是我,我不是谁的大姑父。
另一句基准台词是:“应该吗?不应该啊。”小说中,这句话是他发病的前兆。王战团的精神失常始于年轻时的一次出海,他热衷于小说《海底两万里》,一心向往着去太平洋看看。出海途中,却牵扯进一起权力纷争而被关在储物仓,直至船只返回港口。
走出储物仓后,王战团就疯了。他看着周遭熟悉却又陌生的景物,嘴上念念有词:这应该吗?不应该啊。

别人觉得王战团疯了,但似乎在王战团心中,是这个世界不太对劲。外界社会与他的内心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偏差,而他选择一根筋儿地往自己内心认可的方向走。
他不接受这个世界划定的条条框框,比如“直呼长辈名字不礼貌”。周正听他背诵《海底两万里》,质疑世界上没有会飞的鱼,王战团说,鱼怎么不会飞,人都会飞,然后爬上房顶,在背上插几根大葱仿制成翅膀就往下跳。
葛优的表演是极其出彩的,他的个人风格让王战团这个角色在疯癫以外,添了一份属于世外高人的“仙风道骨”。
恰恰是这种气质,强烈衬托了王战团和家人们的反差。

这个普通东北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都是“正常人”。他们心眼并不坏,会彼此着想。他们与王战团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接纳并遵从于社会划定的种种规则,并致力于过上在这个游戏规则定义下的好生活。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一家人过年团聚的时刻,王战团在房间转来转去,脱稿背诵《海底两万里》全文,幻想着太平洋的广阔;其他人在一旁,庆贺他的大儿子成功谋取了一份公交车司机的稳定工作。
他们诚然是务实的、正常的。但有的时候却为了追求所谓的“正常”,变得“魔怔”起来。
周正自小口吃,家人们都觉得口吃是病,领他四处寻医。周正喝下一包包苦涩的中药,在舌头上扎针、含着石头说话,并因口吃而自卑、自厌。只有王战团会一次次跑过来甩给他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没病。”

周正(王俊凯 饰)
影片设定中,口吃似乎来自周正自小的心理障碍。他有一对严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父母,经常假以关心之意与管束之名发号施令、施以暴力。
一次周正违反了管束,被父母捉回来数落。密集的指责之下,周正准备开口辩解,却在焦急中愈发口吃。父母见他这样,怒气更上心头,伸手去打他,怪他“话都说不利索”。
《刺猬》最有趣的一点是,它经常把“正常”与“疯癫”在具体情境中对调。正常人变成疯子,而疯子保持了清醒的理智。
比如这时候,在一旁王战团指出了被这些正常人刻意忽略的真相:孩子的口吃,就是被你们打出来的。
面子文化
周正恨他的父母,也恨他自己。
从这个敏感自卑少年的视角,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高压的家庭给予人的深刻塑造。母亲是敏感的、精神过度紧张的,她太过担心周正的健康成长,严令他不许与精神失常的王战团来往。影片中,周正数次鼓起勇气和王战团去游泳或者唱歌,就立刻被怒气冲冲的母亲拽走。
父亲是粗犷的、热衷于棍棒教育的。他从不尝试去体察儿子的内心,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偏偏周正是个敏感的孩子,他与父亲的对抗,构成了他青春期自毁倾向的主要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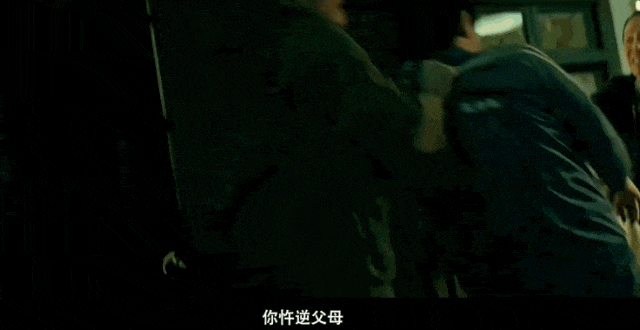
父亲对周正的教育方式粗犷暴力
父母之所以如此教育周正,或许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王战团。他们看见一个“不太正常的人”会如何给家族蒙羞,所以太希望周正长成一个正常小孩的样子。
又或者说,他们因为害怕别人的看法而教育儿子。一个例子是,父亲经常对周正说:“你太给我丢人了。”
与旁人的对比是令他爆炸的引线。周正的同桌来餐馆吃饭,父亲看见她穿着红色的高中部校服,儿子却因初三留级还穿着初中部的蓝色校服,他勃然大怒。

周正的父亲深受“面子文化”之害。他太过在乎外界的看法、评价,被社会对于“什么是好孩子、好学生”的定义卷进去了,深陷其中。而他对棍棒教育的信奉就是这种文化促成的心理畸形。
除王战团和周正之外,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嵌在这套社会准则中。和别人不一样、不符合传统习俗就是丢人的,因此口吃是丢人的,精神失常是丢人的,未婚先孕是丢人的。他们宁愿用棍子抽打一个小孩迫使他向刺猬神下跪,也不愿意听听他的真实想法、反思家庭与学校对他造成的伤害。
哲学家卢梭认为,社会显形之时,就是人类不快乐之始。
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原始人,即自然状态的人并没有贪婪、嫉妒、暴力、仇恨的感觉,他们唯一的自然情感是因别人受苦而心生怜悯。后来,人与人开始合作,以便于互相保护和收益,建立了更密切的关联。随之,人们开始设定彼此的价值,并互相比较、评价,这就是人类之所以不快乐的源泉。
“有个被叫作‘社会’的东西存在于个体之外,那是一大堆规则、关系、禁令和习俗,是人类实现潜能、到达幸福的主要障碍。”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卢梭思想的这句概括,可以准确描述周正与王战团被生活卡住的困境。

片中王战团写的诗则是对其诗意化的表达:“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影片中最令人悲哀的时刻,是王战团送女儿去婚礼现场的路上,突然“清醒”了。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失常和瘸腿会让女儿“丢人”,因此没有出席婚礼。
在这一刻,出于对女儿的爱,王战团接受了这个社会的规训。
在这一刻,我们看见,原来王战团不是个仙人,原来他同样身不由己地被嵌在结构中。
挣脱与出走
对王战团和周正的结局,影片较小说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小说中,王战团死于儿子王海洋葬礼后的第二个月,在精神病院突发心梗。影片中,王战团从精神病院逃了出去,没有人再知道他的消息。
小说中,周正在赵老师的剑指下向白家三爷的牌位下跪,重复着赵老师的指令,向牌位认罪。一袋香灰从他的头顶洒下,周正如释重负,郑执最终写道:“我(周正)再也听不见屋内王战团的呼声了”。
而影片中,周正在牌位前没有下跪,坚守自己的立场,死死对抗。他与赵老师的对抗构成了全片的情绪高潮,故事前期始终缄默不言的少年,愤怒在此刻一股脑儿爆发,向所有人发起复仇。

这个改动是我喜欢的。小说的结尾,“异类们”最终被现实社会驯服了,而影片描写的,是“异类们”的爆发、反抗与出走。
一个令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周正从学校中逃走的时候。操场上,几百名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列成方阵,横成排竖成列,整整齐齐。而周正从方阵中跑过,像一把小刀撕裂了规整的布匹。

周正从学校中逃走
另一边,王战团同样在排队。精神病院和学校施行一样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病人们身穿统一的蓝色条纹病服,挨个领药、喝水送服、张开嘴巴检查,像流水线工厂上的标准化产品。
而王战团把药片藏在手中,悄悄碾碎了。他还在向往大海,宁愿清醒着疯狂,不愿混沌着平静。
过于高压的教育和精神病院是多么相似,在政治学家福柯看来,它们都是一种事先谋好的、控制人们心智的技术性场所,充斥着令人必须服从的机制。它们将人的身体与灵魂分别处置,对身体干预、控制、监视,对灵魂消解、烙印、重置。
最终目的,是造就一群标准化、规格化的“驯服的肉体”。
影片中,王战团和周正最终都逃离了被异化的命运。这个结尾诚然是浪漫主义的,却也是极其具有力量的:它给像王战团和周正一样被生活困住的人们留了一个希望的出口;它愿意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可以挣脱结构的枷锁。

哪怕出走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困局——即使是在驶向太平洋的船只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圈子、规则和秩序。
但只要不丧失与之对抗的勇气,就没有什么生活可以永远卡住你。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奚佑
编辑 | 吴擎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