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作为名人,她不愿将私事公之于众:那会让一个人丢失灵魂
齐鲁壹点2024-06-17 1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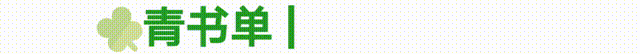
文|安娜·比孔特 尤安娜·什琛斯娜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不喜欢别人窥探自己的生活,哪怕是在身故之后。她从没想过拥有一本“别人为她写的传记”,她一直认为,所能言说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已蕴藏在诗文之中。当辛波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一群记者包围时,记者们从她口中得知,她并不喜欢回答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也无法理解那些什么都往外说的人: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做呢?辛波斯卡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公开谈论自己会消耗内在能量:
将私事公之于众会让一个人丢失灵魂。有些东西应该留给自己。不是所有事都适合被大众知晓。尽管这是当下的一种流行趋势,但我并不认为所有与他人的共同经历都可以拿来贩卖。毕竟,有些经历只有一半属于我。而且我觉得,那些与亲近之人相关的记忆还未最终成形。我经常在脑海中与他们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始终有新的问题和答案出现。我能怎么办,关于自己我只能说这么多。确实有点无情,但是请理解,其他的事并不多,且都是私事,我的、你的、他的……就像秘密文件夹。没什么好说的。我当然对自己做过的不好的事了如指掌,我对自己的意见也不小。我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都不满意,起码对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不满意,但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事,我没办法在公众场合讨论,因为这会消耗我的内在能量。我尝试在诗中——至少是一部分诗中融入一些个人经历。有时可行,有时不可行。但是直接说出那些事不是我的风格。
辛波斯卡对我们说过:“我是一个老古董,在言说自己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要刹车,或是有抵触情绪;又或许正相反,我是个先锋派,没准在下一个年代,对着大众袒露心声的潮流将不复存在。”
诗人乌尔舒拉·科齐奥乌曾说,她与辛波斯卡之间的谈话经常是这样开始的:“现在我跟你说说我的生活。”这是她们之间的私人玩笑,是交流的标志,她们彼此理解,但她们的友谊并非建立在相互袒露心声上。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就是在人生的前73年里,辛波斯卡接受过的采访不超过十次,大部分都十分简短,其中并没有足够多的信息能够支撑起一部人物传记:辛波斯卡没有给出事实,也不记得日期。这也难怪在字典词条中,她的官方简介少得可怜。
波兰语言文学教授、诗人爱德华·巴尔切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打算为辛波斯卡写一部传记。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他也向辛波斯卡本人寻求过帮助,希望她能帮自己整理一份简短的生平大事清单。巴尔切然事先强调不用写任何私人信息,只须提供类似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国、与哪家杂志在何时开始合作以及何时结束合作关系等信息。辛波斯卡在他的要求下越来越不耐烦,最后摊牌道:“既然您读了我的诗,那您就应该知道我对这类问题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巴尔切然没能完成这部传记,尽管辛波斯卡最终提供了自己的生平大事清单和创作年表等必要的信息。巴尔切然试图在纸堆中帮我们寻找那些资料,但没有找到。而且,他后来完全站在了辛波斯卡那边。1995年,当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授予辛波斯卡荣誉博士学位时,巴尔切然在典礼上说:“凡是读过《写履历表》这首诗的人,以后在面对任何跟人力资源部门打交道的工作时都不会再有心平气和的感觉了。”
写份申请书,就得附带履历表。不管人生多长,履历表必须短。应该精简,而且对事实要进行筛选。用地址代替风景,用无可动摇的日期代替模糊易变的回忆。所有的爱情里只算结婚的那个,所有的孩子里只算出生的那些。谁认识你比你认识谁更重要。旅行也只写出国的。隶属什么组织,不用写理由。还要写勋章,但不用写贡献。用一副从未与自己对话、一见到自己就远远躲开的样子去写。沉默地略过狗、猫和鸟,还有尘封的纪念物、挚友与梦。——《写履历表》,出自《桥上的人们》(1986)
当我们着手写作《尘封的纪念物、挚友与梦: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诗传》这本书的时候(它的第一版是在1997年出版的),对人物自传所需细节的寻找始于《非必要阅读》。这本书是辛波斯卡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连载或发表于各类书评专栏的文章合集,它们先后刊登在《文学生活》《文稿》《奥得河》《选举报》等刊物上。这些文本出人意料地提供了许多关于辛波斯卡本人及其品位、观点和习惯的信息。
辛波斯卡欣赏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不喜欢玩《大富翁》游戏,不喜欢噪声,不屑于看恐怖片,是考古博物馆的常客,难以想象别人家的书柜里没有查尔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深爱米歇尔·德·蒙田,爱读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不喜欢拿破仑,欣赏细节控,不认为谚语是民族的智慧,认为叶螨是最傲慢、最有魅力的生物,常用半躺的姿势写作,是检索、注释、引语、符号、超链接、索引和参考书目的爱好者,有时会去看歌剧,对鸟、狗、猫及整个大自然态度友好,坚信人类在宇宙中独一无二。除此之外,辛波斯卡还喜欢过博洪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她喜欢的导演有费德里科·费里尼,也曾是艾拉·费兹杰拉的狂热粉丝,一度想为她写一首诗,但只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后来还是为她写了一首诗,但那已经是21世纪的事了)。她还喜欢乔纳森·斯威夫特、马克·吐温和托马斯·曼——后者是唯一一个她直接在诗中致敬过的作家。回想青年时期读过的书,辛波斯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托马斯·曼的存在被辛波斯卡誉为一种奇迹,她还因其存在而歌颂大自然的进化:
没错,大自然允许这样奢侈的场景出现,比如哺育幼崽的鸭嘴兽。它也可以不让这样的景象出现——而又有谁能够发现,自己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而最好莫过于,它略过那一刻:一只哺乳动物出现了,他的手上完美地武装着一支万年笔。——《托马斯·曼》,出自《一百个笑声》(1967)
尽管我们可以从《非必要阅读》和一些诗文中获得不少信息,但真正填补了辛波斯卡履历上那些空白的,是她不同时期的熟人和密友所讲述的故事(我们有幸结识了上百个这样的人),以及一些老照片。通过这些材料,我们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位热衷于创作五行打油诗,并勤奋地拼贴明信片以替代书信寄给亲友的作家。这些明信片上画着的有运动员,有在空中飞翔的天使、漂泊的鬼魂,有起舞的芭蕾演员,有伸懒腰的猫,还有向地面倾斜的比萨斜塔,有时还会出现与她的某些诗相关的主题,如类人猿或是叩问存在问题的尼安德特人,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收信人读得懂的文字。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是诗人和翻译家,在出版了汇编多部经典的文集《上帝、象鼻与祖国》之后,他收到了辛波斯卡寄来的大象明信片,上面写着“一看就知道是波兰人”;德国纪录片导演安杰伊·科谢克则收到了一个拼贴着闷闷不乐的鬼魂的画作,上面写着“一箩筐的烦心事”。
这部由各种趣闻和照片拼凑成的人物传记变得越来越详尽,我们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事实、事件甚至具体的时间节点,只剩下诗人自己的声音了。而对于会面的邀请,辛波斯卡并没有说“不”(肯定是因为亚采克·库隆为我们写的推荐信),但她也没有急着定下会面的日期。
直到1997年1月,我们于《选举报》上刊登了这本书首版的片段,辛波斯卡才拿着我们理出的树状人物关系图和连她自己都没见过的父母照片,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读关于自己的文字,这感觉很吓人。”她说,“但既然各位已经这样努力了,那也不错,之后我们就让它变得更‘准确’吧。看来你们已经读透了《非必要阅读》。”
1997年年初,当辛波斯卡最终与我们在约定的时间会面时,她表现出了超常的耐心和气度,回答了我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细节问题。她更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增加了一些内容,又修订了一些内容。总的来说,她修改的初衷是不冒犯别人。关于我们写的这本书,她只想表达一个观点:
我以前就知道,我的整个人生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就像一只蝴蝶的一生,仿佛生命只是抚摸了我的额头。这就是我的画像。但这画像又是怎么来的?难道我真是这样吗?我的生活实际上很幸福,但其中又包含许多死亡、许多困惑。但我肯定不愿意讲述我自己的事情,也不怎么喜欢别人言说我的事情。当然,身故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我面对别人时有着另一副面孔,所以他们展示的都是我的趣闻逸事,把我描述成了一个快乐的人,只会琢磨游戏和玩乐。别人这样看我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努力了很久才树立起这样的形象。其实我经常情绪低迷,有很多愁绪,但我不会把它们展示给别人看,我不会展示自己悲伤的一面。你们可以认为我有些精神分裂。在对我友好的人面前,我是一个样,而当我独处的时候,又完全是另一个样:阴沉、痛苦、对自己意见颇多。我时常悲观地认为,诗有时可以陪伴人类渡过苦痛挣扎,却无法避免苦难的发生。
(本文摘选自《尘封的纪念物、挚友与梦: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诗传》)

《尘封的纪念物、挚友与梦: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诗传》
[波兰]安娜·比孔特 尤安娜·什琛斯纳 著
赵祯 许湘健 译
东方出版社出版
辛波斯卡是波兰女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将许多优秀的法国诗歌翻译成了波兰语,并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诺贝尔奖一年后,本书作者安娜·比孔特和尤安娜·什琛斯娜表达了希望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想法。起初辛波斯卡并不乐意,因为她一贯不愿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本书作者以耐心细致的调查和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最终赢得了诗人的信赖。书中不仅包含辛波斯卡本人及其亲密朋友的回忆,还收录了近百幅珍贵的私人照片,近百篇辛波斯卡的诗歌和杂文穿插在文中,并附有作者的精微解读。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