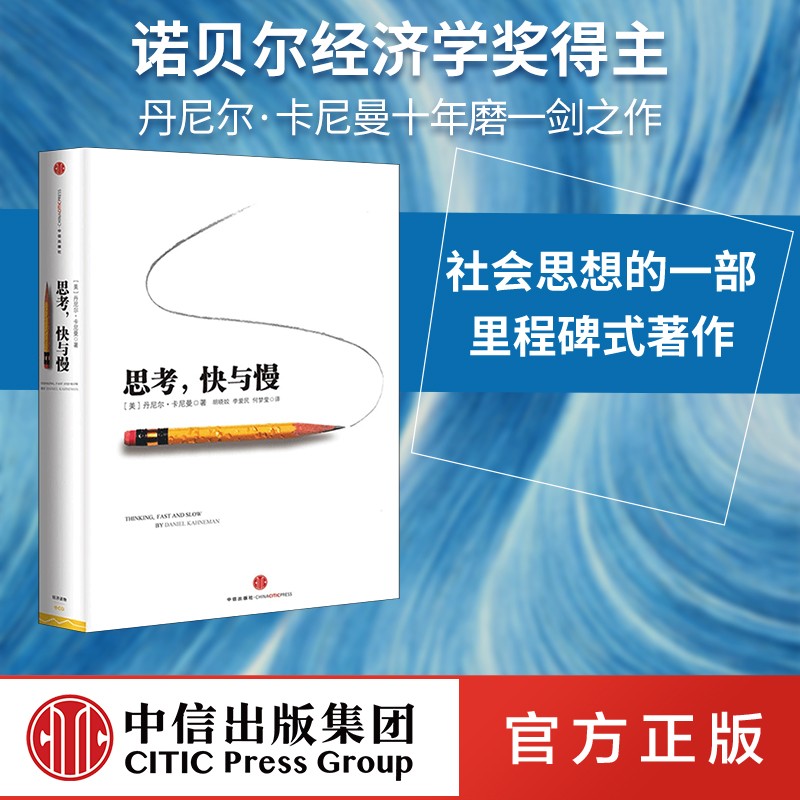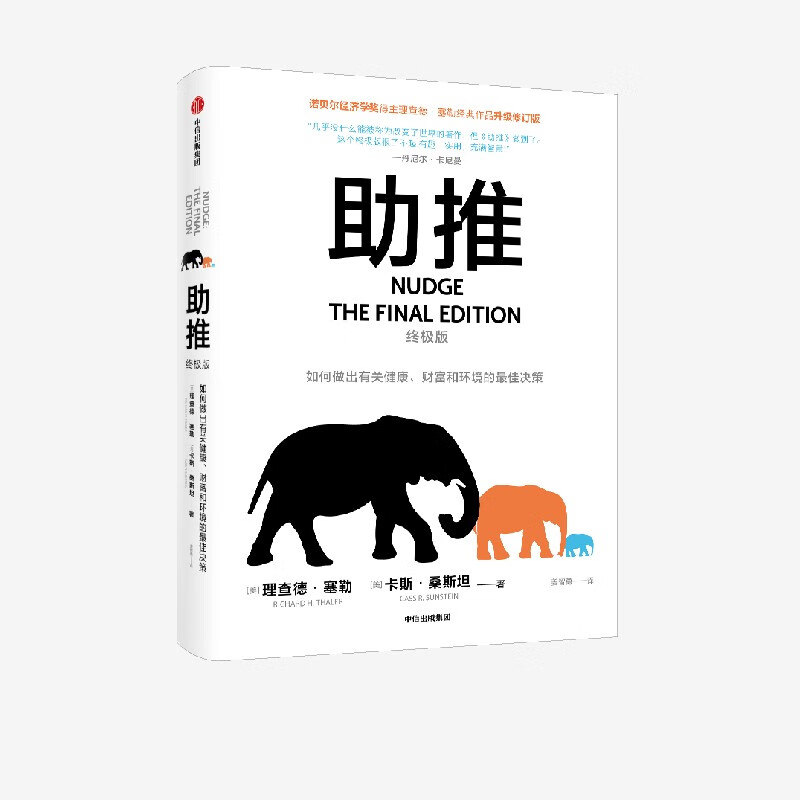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曾评价他是:“现今在世的最重要的心理学家”。
当地时间3月27日,普林斯顿大学发布讣告,该校尤金·希金斯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丹尼尔·卡尼曼去世,享年90岁整。
丹尼尔·卡尼曼(1934·3·5-2024·3·27)
丹尼尔·卡尼曼一生的际遇堪称传奇,对于他学术生涯的总结或许用“著名的决策心理学家”最为贴切,可却因为对人类决策偏差和直觉思维的研究而启发了众多经济学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被誉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其理论和发现包括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损失厌恶、基率忽视等等。尤其是“前景理论”,不仅引发了一场心理学革命,更是打破了学科的藩篱,对经济学、市场营销、公共政策等领域造成了深刻影响。
一个不太恰当却相对直观的比方是,在经济学领域,“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性,不亚于“1+1=2”之于数学的重要性。
但卡尼曼却直击这一经济学的基石,提出——人类是非理性的,我们都会犯很多不合理的错误。
2011年,卡尼曼将自己毕生的思想精华写成了《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信出版于2012年翻译出版了其中文版。这是一本对人类自身根本性问题的全面探究,讨论了“思考”这一活动背后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书中提出的“光环效应”,如今更是成为了中文语境中无人不知的日常用语。
对于《思考,快与慢》的在人类知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黑天鹅》作者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评价最为中肯,他认为当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处于同一水平。
如今,巨匠已逝,但其思想将如一盏知识圣殿中的长明灯,给予一代代后来人以指引。
在一个因AI等科技加持而不得不被裹挟着飞速向前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倾听这位90岁智者的忠告:
思维的速度并不代表其质量。有时候,放慢脚步,深入思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己。
中信出版特出此文,对丹尼尔·卡尼曼致以最高的敬意。
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其成长经历,无疑是我们洞悉其深邃思想的最佳入口。
1934年3月,当母亲正在特拉维夫探亲时,丹尼尔·卡尼曼出生了,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犹太化学家。
当时欧洲所处的动荡氛围自不必多说,一家人先是从立陶宛移居到法国,二战爆发后,父亲又因为其宗教信仰被捕。
一次宵禁时,丹尼尔很晚才回家,路上遇到一名身穿纳粹党卫军黑色制服的德国士兵招手让他过去。
按照当时德国人的规定,犹太人必须将六芒星的徽章佩戴在衣服前胸上。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这个令人感到耻辱的标志,丹尼尔·卡尼曼将衣服反着穿。
出乎意料的是,那名德国士兵非但没有为难他,反而抱着他举起来,用德语热情地说着话,并打开钱包取出一张男孩的照片给他看,另外还给了他一些钱。
这件事连同之后四处逃亡的经历,让只有六七岁的丹尼尔·卡尼曼将“不能相信任何人”从此奉为毕生信条,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活下来。
虽然丹尼尔·卡尼曼说:“人们总是认为童年对人的一生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不确定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
但这些人生阅历,无疑成为他今后将人类错误行为作为研究方向的重要人生背景:
为什么纳粹政权在欧洲肆虐时,许多犹太人产生了误判,在有机会逃离的时候却选择留下来?
为什么那名以抓捕犹太人为使命的德国士兵,却未能发现抱在怀里的小孩竟然是犹太人?
1954 年,卡尼曼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他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被分配到心理学部门,负责评估新兵。
21岁的丹尼尔·卡尼曼创立了一套后来被称为“卡尼曼量表”的方法,用于预测应征者在不同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帮助以色列选拔优秀军官。
这套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曾在色列国防军担任5年首席心理师的鲁文·盖尔说:“有一次他们想做些大的调整,但测试效果变差了,所以又恢复了原样。”
关于这套方法的价值,因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关注,而更加凸显。
这就是丹尼尔·卡尼曼,一位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骨子里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对外界的评价极度敏感,对未来充满了悲观。
84岁,已经早就功成名就的卡尼曼在与一位学者聊天时坦言:“我的性情很大程度上是立场导致的,你找不到比我更悲观的人。”
这些性格上的底色,对于们了解丹尼尔·卡尼曼本人及其思想都至关重要。
丹尼尔·卡尼曼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他的搭档阿莫斯·特沃斯基。
两人于1969 年相识,从此开启了一段为期十多年“不算和睦”的卓越合作历程。
这段故事,被迈克尔·刘易斯写进了《思维的发现》一书。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复杂友谊,刘易斯的总结极为形象,他说:
把丹尼尔和阿莫斯放在一起,就像把小白鼠扔进了巨蟒的地盘,可待你回头再看时,却发现小白鼠在滔滔不绝,而巨蟒蜷缩在角落安静地倾听。
小白鼠就是卡尼曼,多疑敏感,缺乏安全感。而那条巨蟒则是特沃斯基,有着极高的理论造诣,为人更加沉稳。
合作模式上,往往是由卡尼曼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仅仅是一个想法,然后特沃斯基会将这个想法规范化、理论化,给出一个科学严谨的结构。很多时候,一些研究成果基本就是,一个人说了开头,另一个人完成了结尾。
两人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题为《小数定律之我见》的文章。
这篇文章指出了人们——包括许多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一个思维偏误:认为小样本亦能反映群体特征,从而错误地用局部代替整体。
从这一发现开始,他们将研究的兴趣拓展到了人类思维领域:在对不确定的世界进行概率判断时,思维是如何运行的?人类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判断错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关于人类判断之谜的探讨,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们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人的大脑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去计算正确概率,而是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他们把这些经验法则称为“启发性”的。
丹尼尔还提出了著名的“希特勒假想”,这一假设如今也会被高频引用:假设,希特勒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了维也纳的一名画家,会怎样?
揭秘人类判断之谜之后,丹尼尔和阿莫斯接着挑战了经济学中著名的“期望效用理论”,这一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人们做决策时,总是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但“效用最大化”、“风险规避”可以解释购买保险等看似有悖于期望值最大化原则的经济行为,但仍然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买彩票。
丹尼尔首先提出“后悔理论”来解释这个悖论以及人类的其他行为。
但是丹尼尔和阿莫斯同样看到,“后悔理论”仍有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面对损失时人们会甘冒风险赌一把。
于是他们完成自我否定,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刚开始取名为“价值理论”,后来又改成“风险价值理论”,并最终定名为“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不仅完全颠覆了人类理性决策的经济学经典假设,也对世界带来了深刻改变。
经济学方面,理查德·塞勒受此启发,开创了“行为经济学”。
公共决策领域,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基于前景理论的框架效应,对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调整,他与理查德·塞勒合撰的《助推》一书,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主张。
基于前景理论,人们发现了市场营销中更多的规律或方法。
二人的合作成果丰硕,但是裂痕却随着学术的前进在不断加深。
阿莫斯·特沃斯基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而丹尼尔·卡尼曼没有,最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
人们把麦克阿瑟天才奖单独颁给阿莫斯·特沃斯基,美国国家科学院新任院士名单上,阿莫斯名列其中已近10年,而丹尼尔·卡尼曼依然榜上无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每一个收益,都会被视为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损失。
思维就是这么残酷,即使是发现了思维运行秘密的两大天才,也会受到“锚点效应”、“损失厌恶”等规则的影响。尽管丹尼尔·卡尼曼并非耿耿于怀之人,阿莫斯·特沃斯基也为自己单独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等事情深感痛苦。
学术生涯的后期,他们之间的分歧多于合作,丹尼尔甚至觉得阿莫斯为回应外界质疑而撰写文章是“无用之事”。
两人最终渐行渐远,于80年代中期“断交”,不再有任何合作。
2002年10月9日,丹尼尔·卡尼曼获悉自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双系统理论最初由彼得·沃森和乔纳森·埃文斯提出,丹尼尔·卡尼曼对此做了区分,将之称为系统1和系统2。
这是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将人的思考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排他的模式:
系统1作为直觉系统,简单快捷,自动化,受情绪驱动,被习惯和经验支配,很难控制或修正;
系统2作为深思熟虑系统,缓慢、理性、有意识,它耗费资源但不容易出错。
通常情况下系统1是自主运行,它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反应和判断,而此时系统2则处于放松状态,特别是一切顺利时,系统2会稍微调整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系统1的直觉性建议。
但当系统1的运行遇到阻碍时,便会向系统2寻求支持,例如遇到“17×24 = ?”,系统1无法给出答案,系统2便被激活来解决问题。
系统1和系统2的运行分别产生了快思考和慢思考,这两种思考方式分别对应了直觉性和严谨性两种特征和性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卡尼曼表示:“在近期的研究中,系统1的直觉性作用比我感觉到的还要大,它才是做出决策和判断的幕后主使。”
那么,系统1的直觉性判断真的可信吗?答案不言自明。
《思考,快与慢》中还列举了更多直觉带来的“陷阱”,例如典型性偏差、小数定律、光环效应、锚定效应、框架效应、禀赋效应等。
想要避免落入直觉的“陷阱”,我们就要激发更慢、更严谨、需要投入更多脑力的思考形式,也就是慢思考。丹尼尔·卡尼曼说,这也是机构比个人更容易规避错误的原因。
在善用慢思考的前提下,丹尼尔· 卡尼曼还分享了一些提高决策质量的具体方式。
书中写到“避免系统1出错的方法原则上讲很简单:认清你正处于的认知领域,放缓并要求系统2来加以强化。”
但丹尼尔·卡尼曼也坦言系统2并非万无一失,系统2犯错通常是因为它无法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保持持续地学习与研究,汲取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对于提高决策质量而言同样非常重要。
大多数以认知偏见为主题的书或文章都包括这样一段简短的段落,通常在接近尾声处出现——类似于《思考,快与慢》中的这段:“关于认知错觉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克服它们。我只能说……情况不容乐观。”
穆勒-莱尔错觉(the Müller-Lyer illusion)
图中有两条两端带箭头的平行线段,一条线的箭头向外指,一条向内指。因为箭头方向不同,下面一条线段看起来比上面的短一些,但事实上长度是相等的。
关键之处在于:即使我们拿尺子量,发现两条线段一样长,并且学习了一番错觉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以后,我们依然感觉一条线段比另一条短一些。
所幸在视觉幻象方面,我们缓慢分析的思维(系统2)能够辨认出穆勒-莱尔情况,并说服自己不要相信莽撞急进的系统1的感受。
然而在真实世界中,当我们面对的不是线条而是日常的人与事件时,就没那么简单了。
“糟糕的是,这些机智的程序在最被需要的时候,也最难被调用。”卡尼曼写道,“我们都希望有一台警钟,每当我们要酿成大祸时它就响个不停,然而你买不到这样的钟。”
“我看到图上的两条线段长度不等。”他说,“这时,目标是对我以为自己看到的东西产生怀疑,是要明白不应该相信我撒谎的眼睛。”对于视觉幻象,这样的目标可以达成,他说,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偏见几乎不可能。
卡尼曼认为,认知偏见最强有力的对手来自外部:比起我们自己,他人更容易觉察我们的错误。
虽然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给出了一系列改善思考的建议。但“我的立场是,这些东西对系统1都没有效果。”卡尼曼说。
“你不能改善直觉。也许经过长期训练、大量交流和行为经济学的学习,你学会了提示推理,就可以让系统2遵循规则运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压根不给你提示。而且绝大多数人在激烈的辩论时早就把规则扔到窗外了。”
关于他的理论,这是卡尼曼给出的一个充满怀疑论的悲观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