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网站近期的报道,健康数据管理公司Harmony Healthcare IT一项新调查显示,在美国,18-26岁的年轻人中有61%被诊断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
焦虑不只存在于美国年轻人中间。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2)》表明,对于中国青年网民来说,学习/工作焦虑在所有焦虑类型中最为突出,此外,青年网民还表现出了“边焦虑边奋斗”的生活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曾撰文指出,年轻人焦虑感增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下降,更深层原因则在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在普遍的焦虑背后,到底有什么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
“破坏性完美主义”诞生,青少年面临高压
心理健康问题正在侵袭青少年群体,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现象。《高压年代》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心理学博士一位是医学博士)通过数据告诉我们,近十年来,美国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率飙升。大学生寻求咨询的比例上升速度高达平均招生人数上涨速度的五倍。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的比例之高,已经堪称流行性疾病,尤其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成年,眼前就是竞争日趋激烈、机会越来越少的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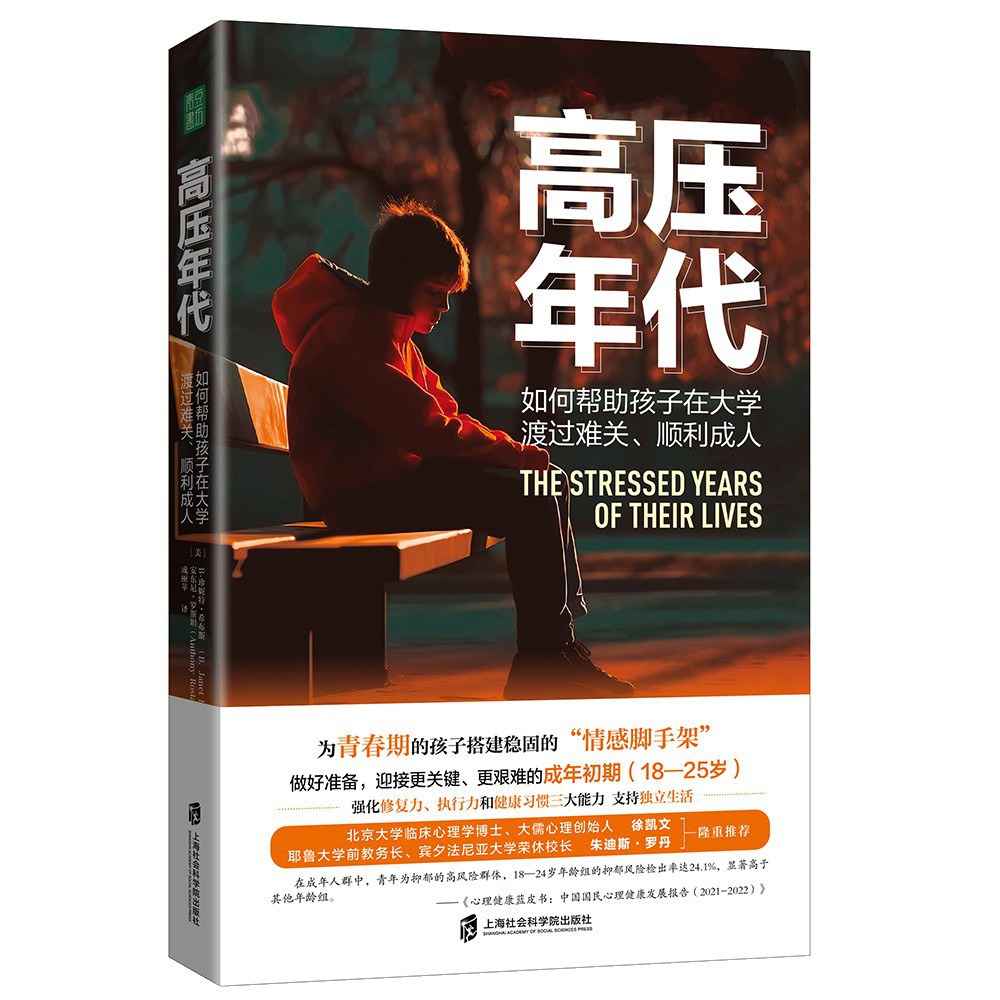
[美] B.珍妮特·希布斯 著 成丽苹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3-07
全球范围内,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哪怕是一直标榜自己有着举世无双的向上流动机会的美国,流动性也已经持续多年下降。社会流动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减少,中产群体的收入安全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们也心怀忧虑,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只有一条直线,“你必须做得好。你不能犯错,否则机会就会被毁掉。”于是,“破坏性完美主义”诞生了——人们无法容忍孩子不能够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色。可是问题在于,人都有犯错误或失败的时候,通常没有谁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色。但哪怕样样都做得不错,学历贬值也成为了现实,大学学费花费高昂,有时价值甚至只相当于过去的高中文凭。
持续的焦虑,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征
为何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在降低?为什么人们感到不确定性正在增加?《朝不保夕的人》作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看到,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得风险和不安全性转嫁给了劳动者及其家庭。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之一是各国需要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弹性包括很多面——工资弹性意味着加快调整薪资(特别是降薪)来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雇佣弹性意味着企业可以轻易调整(尤其是减少)雇佣人数,无须付出代价,雇佣安全和雇佣保障因此被弱化;岗位弹性意味着企业可以在内部以最小的反对力量和成本调动员工岗位、改变工作结构;技能弹性意味着能轻松调整劳动者的技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因为市场缺乏弹性,劳动力市场缺乏“结构性变革”,而所谓的“弹性”本质上就是系统性地降低员工的生活安全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人进入“不稳定的生存境况”中,意味着他们在未来几年、几个月或几周里都无法保证自己和现在从事同样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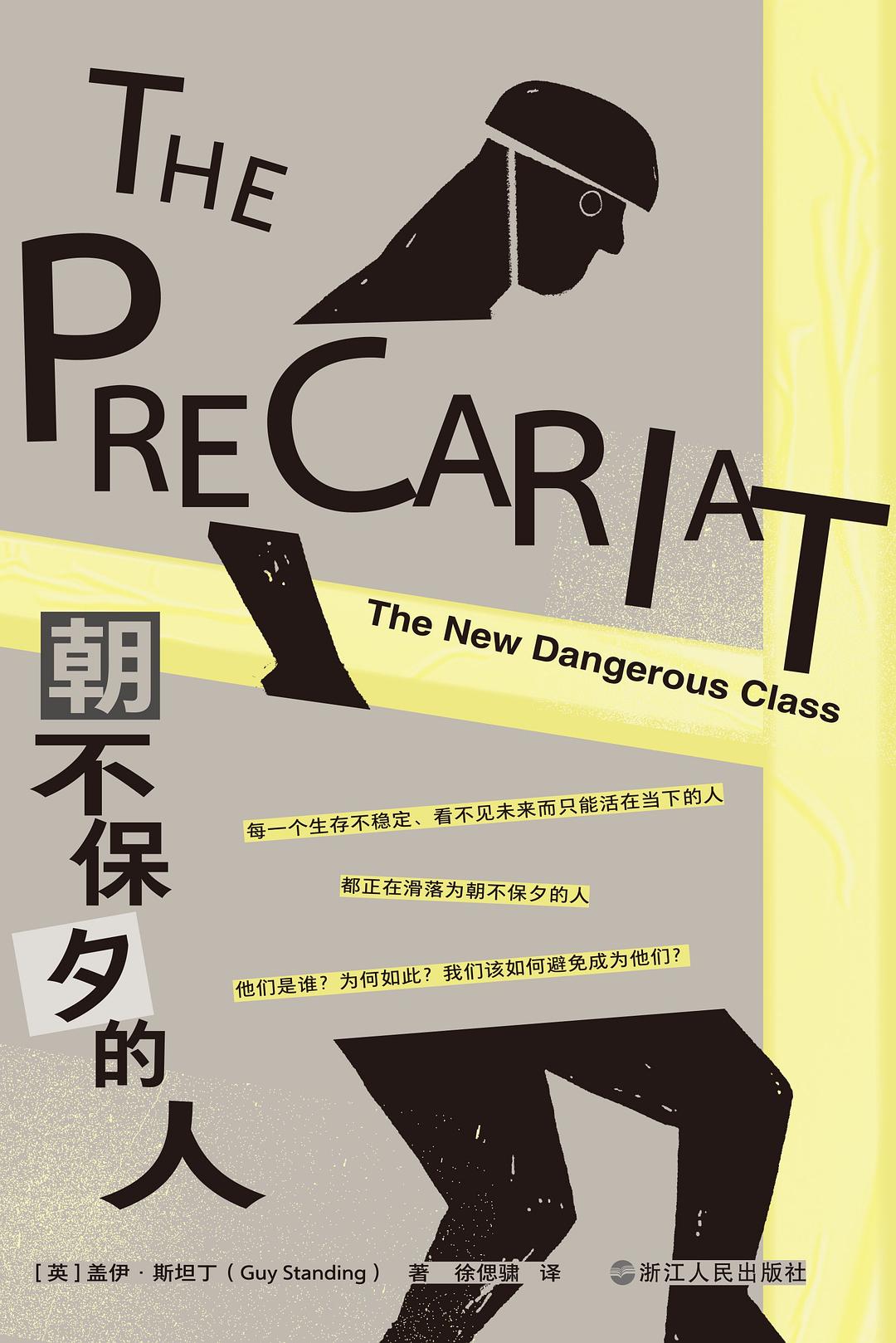
[英] 盖伊·斯坦丁 著 徐偲骕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04
如今,企业商品化越来越显著,这意味着企业主做的承诺不如过去有价值。企业主明天就可能和经营团队一起离职,之后,关于劳动内容、工资给付、员工遇到困难时企业该如何对待他们等问题的协商也会一并失效。企业商品化使得哪怕是白领阶级也会在一夕之间失去工作和其他保障。企业为降低风险、控制成本,会想要更有弹性的劳动力。在全球化体系中,临时劳动力带来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大,各种企业纷纷效仿——例如,麦当劳的模式就包括制作流程的去技能化、解雇老员工、打击工会、降低公司和削减企业福利,其他公司随之群起效仿。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雇佣临时劳动力,这也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环。
其结果就是创造出了一个全球性的朝不保夕群体。按照盖伊·斯坦丁的预估,目前在很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朝不保夕者面临着不安全雇佣、短期岗位盛行、劳动保障匮乏的问题,同时也丧失了过去工业无产阶级和白领领薪阶级眼中应得的权利——职业生涯的概念、稳定的职业身份、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持续的焦虑就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征。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2011年以来,焦虑的发生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本质上,焦虑的增加并不只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分配的问题,是结构性不平等的表征。有英国研究者认为,焦虑症发生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衰退和国家实施的紧缩政策,另一项研究认为福利改革和精神疾病的增加密切相关。
碎片化工作摧毁长期纽带与目标
是否只有“临时工”或同时打着几份工的人,才有朝不保夕的焦虑呢?其实,标准雇佣关系这种绑定的关系正摇摇欲坠,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正在不断扩大。许多岗位在浪潮中开始重组,加重了朝不保夕群体的扩大,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经理人职业的商品化,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劳务中介机构或者招人担任临时经理来完成一些短期任务,许多临时经理人从颇有地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沦为了“用后即弃”的人。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周悟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10
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客座教授、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发现,哪怕是对硅谷计算机行业的精英来说,“短期聘任”(NO LONG TERM)的工作制度也会让人时时感觉到危机,陷入另一种焦虑:因频繁换工作而不得不多次搬家,自己及家人都不再拥有和外界的长期纽带,甚至没有机会去建立这样的纽带;他们难以在工作中稳定自己的职业形象与身份价值,更难以应对外界的人际需求与自我的目标追求。
弹性制度会引发焦虑,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哪些风险可以得到回报,也不清楚究竟该踏上哪一条路。每个人都可以被替换,随时拎包走人,脱离团队,加入另一个团队,这样的碎片化工作经历,也使得人们失去了对工作的依恋、失去对某个进展缓慢但有意义的工作内容投入的信心。“整个制度在缺乏互相信任的组织中散发着冷漠。其中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被需要。这样的冷漠正是在一次次企业再造中实现的,因为员工被利用之后便被弃之如敝屣。”
弹性资本主义也会给人们的品格带来问题——在这样一个心浮气躁、只看眼前的社会里,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是自我内在的持续价值?在专注实现短期目标的经济体系里,怎么才能追求长期目标?在不断分裂重组的机构组织里,怎么维持人们之间的忠诚和承诺?
持续精疲力尽,成就求而不得
面对以上问题,个体何以应对?“鸡娃”有没有用?“卷”有没有用?婴儿潮世代的尾巴和最早一批X世代的青年生活在平稳向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然而他们的子女“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参加工作时却普遍感觉倦怠。
文化研究学者、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看到,与父母一代相比,千禧一代拥有的是少得多的存款、糟得多的社会平等、差得多的稳定性,以及极重的助学贷款。她将千禧一代遭遇的倦怠描述为一种持续精疲力尽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高中老师批改考试试卷的状态,或者是快餐店工人下班后开网约车兼职的状态。这种倦怠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视为一种职业现象,是长期工作场所压力未得到成功管理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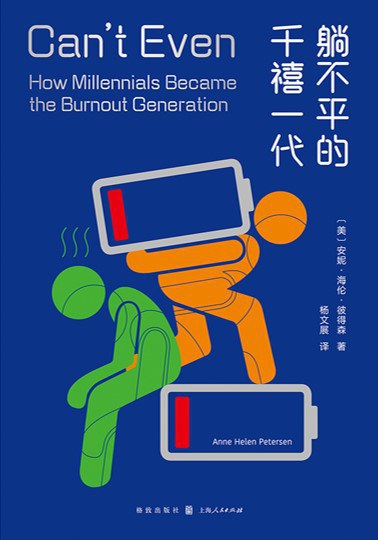
[美]安妮·海伦·彼得森 著 杨文展 译
格致出版社 2023-10
和拥有自由放养式童年的婴儿潮世代及X世代不同,千禧一代从小进入精细育儿的流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娃”。他们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为了完成一项又一项的目标,从小到大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抱着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这类想法的他们,却先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由于20世纪后几十年的经济大衰退、技术驱动的零工经济崛起、对工人保护措施的不断减少,许多2008年后进入就业市场的工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工作场所不止一个。于是,千禧一代从压力大、日程安排过多的孩子,变成了精疲力尽、过度劳累的成年人。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发现,对于千禧一代人来说,效率就是生命,他们已经内化了应该不停工作的想法,从小的自我优化使得工作和娱乐的边界早就模糊。
然而,工作完成得越多越高效,工作条件反而变得越苛刻、收入更低、福利更差、岗位更不稳固。高效没有换来更高的工资,坚韧没有提高价值,对工作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剥削。与这种精疲力竭相伴而生的还有对成就感的强烈渴望。人的内心总是充斥着难以抑制的欲求和焦虑,让这种渴望变成了痛苦的求而不得。然而,冷漠的现代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努力无动于衷——以前,年轻人掌握了一项技能,几十年后就会带来回报,但是如今人们发现,花费了很多年取得的资格证书,已经过时又不够用,参加的培训越多,掌握的技能反而越可能赶不上业界的进展。面对技能被淘汰,人们要么疯狂学习技能“卷”,要么认为反正无论如何都无法带来确定回报就干脆不作为。接着,复杂的分工和高科技使专有技术不再属于任何职业,而只存在于支配人的程序之中。每个员工被设计成可被替代的,在一次次企业再造中被舍弃,讲究个人品格、相信工作的意义、不断提高技艺并成为不可替代的行家已经是上一代的传说,这削弱了人的价值感。
然而在美国,“过度工作”(overwork)的工作伦理已经变得标准化。作者在人类学家何柔宛对咨询公司的田野调查中找到了直指驱动倦怠文化之引擎的话:“没有什么比能不断干成事更好的了。”任何妨碍“干成事”的行为,都被理解为缺乏奉献精神或工作伦理,甚至被强烈暗示为缺乏智慧。但是,这种心态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精英主义,同时,却也丝毫没有质疑精简规模、裁员和外包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