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
编辑 | 林子人
中译版《那不勒斯四部曲》编辑索马里曾经谈到:“对于任何一个无法从‘那不勒斯四部曲’小说全身而退的读者而言,他对HBO联合RAI(意大利广播电影公司)电视剧改编的标准极有可能是:page-to-page(逐页改编)。”作为埃莱娜·费兰特最忠实、最虔诚的粉丝,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一、二季的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改编这部作品注定是一场工程浩大而又野心勃勃的致敬。自2018年11月剧集在HBO开播以来,导演科斯坦佐便受到来自各方的瞩目与压力,《纽约客》《纽约时报》《卫报》《名利场》等多家媒体几乎以每两集为一个单位对科斯坦佐的影视改编发布长篇评论,关于“文学原著与影视改编”之间关系的探讨,亦在这场褒扬与挑剔持平的舆论浪潮中持续发酵。
日前,木心美术馆馆长陈丹青在“我的天才女友-当文学成为影视”特展现场,与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Saverio Costanzo)、意大利影评人马克·穆勒(Marco Müller),意大利女演员阿尔芭·洛瓦赫(Alba Rohrwacher)等进行连线对谈。尽管评论家们极度热衷于将最终的影视呈现与原作文字进行比对,从宏观气质到具体细节都无一疏漏,但科斯坦佐却在谈话中表示,自己在与费兰特的邮件通信中从未受到过她在任何方面提出的限制。科斯坦佐坦言,费兰特本人对这次的改编颇为满意,“她是一个非常严肃,严格,但又非常包容的人。”费兰特甚至告诉科斯坦佐,“人物越接近于你的想象,就越接近于我的想象。”
谈影视改编:“被稀释的痛苦”与“被放大的暴力”
《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的最后一个镜头已向观众暗示了,第四季的“埃莱娜”将由意大利女演员阿尔芭·洛瓦赫接替玛格丽特·马祖可出演(据科斯坦佐称,中年莉拉的扮演者尚在搜寻之中)。对于视觉的艺术而言,旁白的大量引入也许是危险甚至是致命的,然而陈丹青和影评家穆勒却对贯穿于剧集始终的、由洛瓦赫配音的旁白赞赏不已。洛瓦赫的画外旁白如同“幽灵费兰特”的分身在场一般,使得这场由文字向视听的“转译”更为细致和准确。
当被问及“如何诠释好人物的那不勒斯性”时,洛瓦赫表示,虽然自己从未有过在那不勒斯生活的经验,但是“埃莱娜”身上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女性印记”足够帮助她更好地理解角色:“埃莱娜一直想要逃离自己的出身,通过教育实现阶级的跃升,她一直想要消除存在于自己身上的过去的印记。”这条女性成长路径既是50至70年代女权运动高涨时期那不勒斯女性的历史出路,亦是所有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共享的普遍经验。穆勒认为,洛瓦赫的旁白以一种睿智、平和与温柔,中和了埃莱娜正在经历的现实的残酷,一种来自“事后”的视角以其更成熟的思想性,缓和了埃莱娜当下的痛苦,使得剧中传递的苦痛与柔情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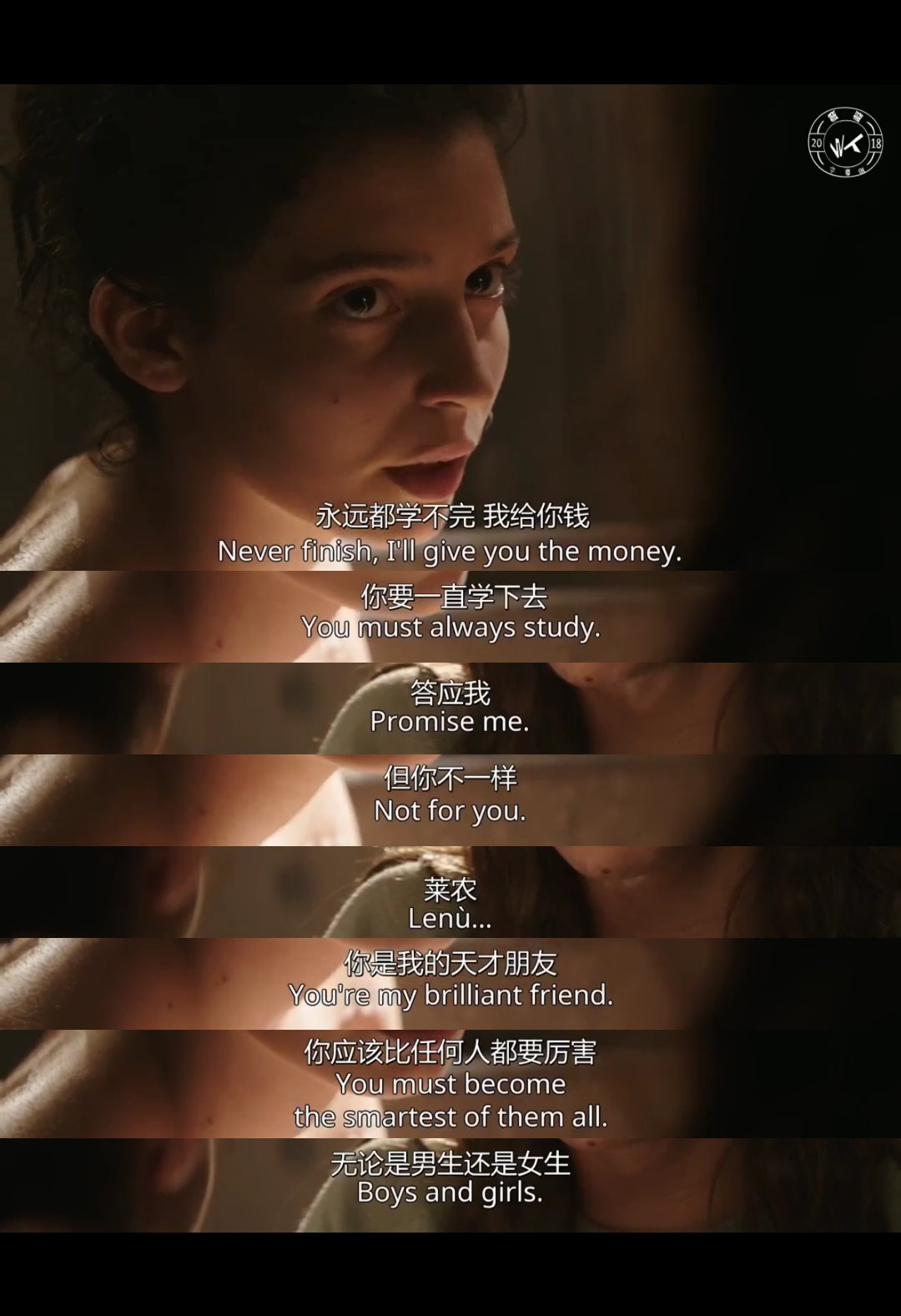
然而在旁白以外的其余部分,科斯坦佐却并未在所谓的“艺术的平衡”中美化现实的残酷。在呈现原著小说中费兰特所描绘的“来自大地深处的”、“贫穷、肮脏的光”,抑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诗意文字时,镜头的语言也许是苍白和无力的,但在呈现意大利底层社会的暴力与恐惧时,科斯坦佐的视听语言却有着出奇锐利的力量,它甚至为我们填充了许多被费兰特自己也忽略的东西。科斯坦佐将寄生于那不勒斯底层街区的暴力通过视觉加以强化,让暴力变得更为缓慢、可见、明晰。
奇妙的是,在小说原著中,费兰特对暴力的描绘秉持着一种接近于自然主义的“如实描绘”的笔法,而对于一个习惯了压迫与暴政的女性而言,她能够给予残暴场景的注意力也许只是略带麻木的一瞥。例如在小说的第一部中,帕斯卡莱的木匠父亲被堂·阿奇勒的打手狠狠摔到墙上的场景,以及安东尼奥为保护妹妹艾达而被拳打脚踢的场景,在小说中都只是寥寥几行的轻描淡写。而科斯坦佐从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就致力于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填补、扩充观众对于暴力与压迫的感受。
科斯坦佐在观众提问环节谈到,对他而言改编时真正的困难也许是对“性的暴力”进行影视化的呈现:“原著小说在描写性时涉及到很多暴力的成分,在影视中,怎么样去表现女性在性中受到的暴力,怎么样让男性的粗暴与女性细腻的感受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莉拉婚礼当夜的性暴力场景也许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改编案例。丈夫斯特凡诺不顾莉拉的意愿(婚内)强奸了她,在小说中,诗意的文本是这样叙述莉拉眼中的恐怖的:“堂·阿奇勒正从这个城区的泥潭里复活,附到了他儿子身上。堂·阿奇勒正在从斯特凡诺的皮肤里冒出来,正在改变他的目光,正从他的身体里爆发出来。”而电视剧的改编则巧妙地利用了“玻璃门”这一道具。斯特凡诺隔着浴室的门,觊觎着作为欲望客体的莉拉,玻璃门将本该亲密无间的夫妻分隔开来,呈现为“入侵者”与“抵御者”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斯特凡诺的脸映在凹凸不平的玻璃门上,妖魔化为噬人的野兽,在三次反复出现的特写镜头中,这张脸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表现这场充斥着恐惧与压迫的性场景时,科斯坦佐与费兰特一样,没有聚焦于对性行为本身的表现,而是通过几组频繁切换的正反打镜头和隐匿现场的拍摄手法,侧面刻画男性的残暴。
谈电影:《我的天才女友》是继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后意大利最接近世界中心的一次
科斯坦佐谈到,他试图以那不勒斯的时代变革为线索,来呈现剧集风格从第一季到第三季的变化。在第一季中,科斯坦佐更多地采用了新现实主义“深度挖掘苦难、呈现真实生活”的艺术风格,来处理底层社会的贫穷与压抑,在叙述“那不勒斯童年”的这一季中,零星的几点欢乐与深厚的苦难相比显得尤为稀薄和脆弱。在第二季中,科斯坦佐将意大利60年代动荡的政治背景全面纳入了情节之中,这种对于那不勒斯公共空间的全景式描绘在第三季中逐渐收束,叙述转向展现以莱农为中心的家庭空间,女性的婚姻生活、欲望诱惑以及创作者的成长之路成为第三季的关注焦点。

对五六十年代那不勒斯方言的坚持使用,亦是科斯坦佐建构“那不勒斯性”的核心策略:导演不得不在前期对大量非专业演员进行长期训练,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剧中说出一种纯正的“1950年代那不勒斯口音”,即便是当代的意大利观众也只能凭借字幕理解剧中台词。这并非无意义的坚持,事实上,“那不勒斯方言”在这场关于变革的叙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小城方言、拉丁语、希腊语,剧中所有的语言符号背后都指向悬殊的阶级与身份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该时期底层渴望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莉拉”这一富有意大利神话色彩的女性形象,亦成为了剧迷们通向意大利过去历史的核心窗口,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引导着当代女性对于“属于女性的变革力量”的想象与反思。在互动环节中,有女性观众谈到莉拉形象与古罗马传说中的“狄多女王”间的隐喻关系,她认为莉拉身上蕴藏着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的力量、创造的力量,犹如“狄多女王”的现代化身。莉拉代表着一种必然要发生的破坏与开拓,一种毁灭性的激情与力量,却也最终毁灭于自身的这股危险力量之中。科斯坦佐亦回应道,在即将迎来的第四季中,莉拉身上的这层神秘的神话隐喻色彩将愈发突显,“莉拉有一句台词的大意是,她只是利用了这些男人,但从没有真正爱过他们。这时的莉拉就像狄多女王一样,在关于古罗马帝国的建国传说中,是女王利用了与埃涅阿斯的绯闻,迫使他去建立了一个罗马帝国。”
陈丹青在活动中多次表示,一部讲述那不勒斯、讲述意大利故事的剧集能够激起如此多当代年轻人的瞩目与痴迷,这是最令他感到讶异和欣喜的。“作为埃莱娜和莉拉的同辈人,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对于中国导演和观众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年轻时被意大利电影吸引,被法国新浪潮吸引,但后来,我更多地被英剧和美剧转移了注意力,有时候我在想,70年代前的那个欧洲去哪里了?”陈丹青在其他场合也曾表达过新媒介对于传统艺术形式的撼动,他谈到,美剧成了21世纪的长篇小说,因为“人的欲望是听故事,最好的故事是活人现身”,曾经的绘画、文学和电影哺育了今日的影视,而如今,大众的欲望迅速扑向了新媒介,“许多老媒介被新媒介灭了,许多艺术的类型过时了,消失了。”
因此在陈丹青看来,《我的天才女友》最为迷人的气质便在于它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弥漫着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电影和黄金时代欧洲文化的怀旧情绪。这种对影视上的“欧洲”的重新唤醒让陈丹青认为,《我的天才女友》与其说是电视剧,不如说是“加长版的欧洲电影”。作为美国鼎级剧场HBO制作的首部小语种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的热映也许是继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人开创的黄金时代之后,意大利最接近于世界中心的一次。

在对谈中,陈丹青也向导演科斯坦佐发问:如今制作精良的英剧和美剧对于世界观众的统摄性影响,早已取代了70年代以前的欧洲电影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否那个电影史上璀璨的欧洲在70年代后就逐渐衰落了?科斯坦佐否认了关于欧洲电影衰落的论调,他谈到,意大利老电影的魅力是世界电影艺术的一块基石,全世界的电影都曾经享用过、也正在享用着它丰富的遗产。“在第二季的拍摄过程中,很多时刻,我都联想到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在整个第一、二季中,映照在人物脸上的吝啬的光线,与肮脏、荒芜的街区环境,的确极易让人联想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1964)中那片废弃、压抑的意大利土地,以及贯穿于其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疏离、孤独的情感关系。科斯坦佐表示,在私心上,他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天才女友》,与世界观众一起,重回那个属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的时代”。
